|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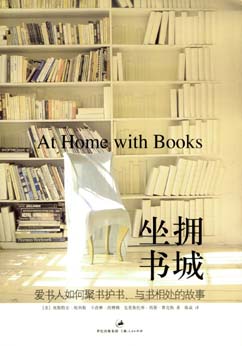 由美国三位藏书家编著的新书《坐拥书城:爱书人如何聚书护书、与书相处的故事》(埃斯特尔·埃利斯等著陈焱译)近日出版。 由美国三位藏书家编著的新书《坐拥书城:爱书人如何聚书护书、与书相处的故事》(埃斯特尔·埃利斯等著陈焱译)近日出版。
这是一本让爱书人爱不释手的书,图文并茂地记述了四十位书迷雅士和他们的书房,他们嗜书如命,书卷盈室。书可聚人,历史作家芭芭拉·塔奇曼说:“没有书,历史会喑默,文学会失音,科学会瘫痪,思想会停滞。”
为什么我们对书籍一往情深?
“灵魂之药房。”
——古罗马图拉真大帝广场图书馆的铭文
为什么我们对书籍如此一往情深?为什么我们一生大量聚书,毫无节制?我们的藏书除了用作求知,还有更多象征意义——书籍便于携带,价钱适中,又赏心悦目,把我们与过去、现在和将来相连。芭芭拉·塔奇曼写道:“没有书,历史会喑默,文学会失音,科学会瘫痪,思想会停滞。”我们对书的那种难舍难分之情,似乎是与生俱来,即使是信息革命和电脑光盘的侵入也未能取而代之。
拾级而上的书架,连接两间房的书廊,把一个房间分成两半并分隔成开阔空间的书墙,从门廊到阁楼天窗的书,把房间全占满了。藏在嵌镜大门后面、保存了作家的个人记忆和创作隐私的书,浴室里的书,摆在靠墙桌子上准备处理的书,堆放在床头小几上平时倚枕阅读的书……书就像小孩子,总是那么缠人,总是那么可爱,可有时又让人受不了。
入主白宫的好几届美国总统及其家人都爱书。例如克林顿夫妇就泛览群书,从政治科学到惊险小说,全都囊括。他们初进白宫时,首先注意到的事情之一就是发现书架不够多。他们明白,没有自己的书,白宫绝不会有家的感觉。
还有一个例子是大学校长哈罗德·夏皮罗的轶事。他从密歇根搬到普林斯顿大学去担任校长。搬家前,他的妻子请了一个研究生帮忙把他们夫妇俩的几百本藏书编目和装箱。他们决定按主题来分类,比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科学、游记等等。她说:“这样便于我们使用。”可是到了后来,离那次搬家多年之后,夫妇俩又积聚了大量新书,此乃学者所熟悉的职业“危险”。这些书该怎么处理呢?她笑道:“我们只能把另一间房变成书房了,呵呵。”
谁没有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呢?什么是存放藏书的最佳方法?有人认定应按字母顺序,也有人主张按主题,大多数人说应该把书装箱放在地下室。有些注重视觉效果的人甚至更极端,要按书籍封面的颜色来摆放。薇薇安·夏皮罗认为,她的新书房要启迪人的心智,要与最新出版的新书隔绝。所以要采用另一种分类法——按书的出版时间存放。不断拥有新书,永无止境,爱书人仍是左右为难。
时至今日,书籍遭到了新的威胁。电脑科技让人能从各种浩瀚来源中检索到信息,一张光盘即可复制并呈现在屏幕上,这似乎预示着靠书来学习将很快成为一种过时的方式。很多大学出版社和图书馆都认为书籍出版业可能难逃劫数,终将变成生产磁盘和光碟的电脑化厂家。到二十一世纪末,今天我们熟知的图书馆会像静止摄影或食品库一样,终将变成明日黄花。
美国国会图书馆前馆长詹姆斯·哈德利·比林顿认为图书馆是高贵的公共机构,他对此奋勇捍卫,并大声疾呼:“一个人不管在世上从事什么职业,居住在何处,图书馆都是他们求学之旅的起点。阅读本身就像冒险,而图书馆就是我们的大本营。”他的继任者丹尼尔·布尔斯廷也说:“书籍便于携带,翻开就能阅读,又各有特色,在今天而言,或者就所能预见的技术而言,仍然无可匹敌。”即使新闻周刊互动公司主编暨总经理迈克尔·罗杰斯这类使用光盘多媒体的先锋人物也不得不承认:“说到要表达观念的纯粹力量,没有东西能胜过文本。”
光盘与书,孰优孰劣?不免有争论。女作家弗朗西丝·菲茨杰拉德说了一句言简意丰的话:“磁盘和书不同,你总不能带一张软盘片上床看吧?”我们同意她的看法,这里叙述了多位爱书人如何为爱书魂牵梦绕,还描写了因藏书而形成的那种相亲相迎的气氛,有时候,这种气氛甚至超过读书的乐趣。
藏书入门须知
按照鲍曼珍本书店老板纳塔莉·鲍曼的说法,如果你想成为藏书家,开始时又受到地方和金钱的局限,藏书之初有个好办法,就是选定一个特定的领域(医学、科学、文学、历史)、特定的时期(美国革命、古代世界、十八世纪)、思潮(女性研究、美国黑人历史)或特定的主题。按照这种方法,无论有何限制,搜集书籍时既能巨细无遗,又有所侧重。等到你认为自己已位居藏书家之列,即使是数量不多、珍本欠奉,接下来也更容易以切合实际的方式整理藏书,因为此时已确定好收藏的目标。
“私人书斋”公司的老板库尔特·汤美茨为如何管理藏书提供咨询服务。他也同意这种专门化的收藏方式是目前最好的途径。对业余人士而言,考虑到钱财和书的来源,多数收藏珍稀本的其它方式并不可行。收藏现代小说的初版本曾是风行一时的主题,但由于收藏者越来越多,已经失去了吸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