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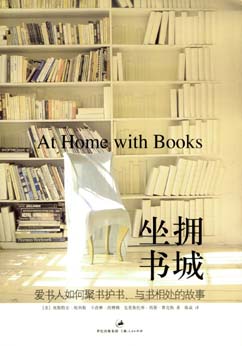 书可聚人。书的作用并不只是联结读者和作者、联结读者和朋友。书在我们的意识形态和地域的不同世界之间搭建桥梁。古往今来,书一直就有此功用。我们的书房所呈现的不只是学问知识,它们还把我们与过去、现在和未来相连。用获得过普利策奖的历史作家芭芭拉·塔奇曼的话来说:“没有书,历史会喑默,文学会失音,科学会瘫痪,思想会停滞。” 书可聚人。书的作用并不只是联结读者和作者、联结读者和朋友。书在我们的意识形态和地域的不同世界之间搭建桥梁。古往今来,书一直就有此功用。我们的书房所呈现的不只是学问知识,它们还把我们与过去、现在和未来相连。用获得过普利策奖的历史作家芭芭拉·塔奇曼的话来说:“没有书,历史会喑默,文学会失音,科学会瘫痪,思想会停滞。”
此次应邀为中文初版的《坐拥书城》撰写序言,我深感荣幸。《坐拥书城》是我的第一本书,成书距今已逾十年,发行了十二个版次。此书在世界各地都有读者,说明了书对每个人都有吸引力,书对每个人都有价值;也说明了能丰富生活和装饰住宅的个人藏书室正越来越有必要。我希望借助《坐拥书城》一书,让中国的爱书人与海外的千千万万的男女相联系,一起分享读书藏书、护书理书、与书共处的热忱。阅读拙著,中国的爱书人能看到人与书共处一室的多种方式,他们在生活中为书营造空间的奇思妙想,还有让他们的家显得美观整洁的摆放藏书的别出心裁。
《坐拥书城》于一九九五年首次出版于美国,如今又在造纸和印刷术的故乡中国出版美轮美奂的中文版。《坐拥书城》的初期几个版本发行于英国,后来又发行了意大利文版和德文版。我也收到了澳大利亚、荷兰、加拿大和法国等国读者的来信,让我深信此书在全球都应该有吸引力,有读者。世人成知中国自古是爱书藏书的国度,迄今有增无减。想到今天我或许会收到中国读者的来函,心情很激动。
据我所知,中国人藏书读书已有几千年,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普林斯顿大学中文善本书同际联合目录总编辑艾思仁教授说:“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很快,国际化加速,对中国的书籍和藏书都有深远的影响。很多各行各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周游列国,得以体验外国的书籍文化。因此,有更多人使用外语,熟习外语,对外文书的兴趣和需求因而大量涌现。如今在中国有很多新的外文书籍译本在出版,这本中文版的《坐拥书城》就是一个例子。”艾教授还鼓励我:“这本书会在中国受到欢迎,找到读者的。”藏书热方兴未艾,一些中国城市因为可供购买的书籍又多又好,像磁铁一样吸引着读者、读书人和藏书家。
据我所知,不是所有中国读书人的家里都有很大的地方来特设一个传统书房,即使到了今天也不是人人都能如愿以偿,这和西方爱书人的情况相似。新一代的读书人已不只在家中的书房读书。我们多数人的住处都是小公寓,家里也不宽敞,所以处处是书,为书环绕,触手可及。而我们也会随处读书:卧室、厨房,甚至入厕读书。看看本书的很多图片就可明白了。按书中琼·瓦什的话来说,她形容自己藏书上瘾,最爱在浴缸里读书。她坦承自己在浴缸里读书的妙思,是受到一位十八世纪的德国饱学之士的启迪。此人把荷马的诗篇印在橡胶上,这样在沐浴时也可吟诵。
读书人都爱讲故事。本书描述了四十来位书迷的书房,瓦什就是其中一位。我同合著此书的卡洛琳·西博姆以及摄影师克里斯托弗·赛克斯一起走访了欧美的书迷。他们对自己,对其珍藏和起居同住的书籍,都有故事可说。有人跟我说:“书塑造了我们。”“人为书设立安身之处,书让家成为家。”“书限定了我们的生活。”“书是我们的生命线和时间线。”
爱书人也是评论家、电视节目评论员的罗杰·罗森布拉特告诉我们,柏拉图去世时,枕头下有一本书;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死时,肘放在摊开的书页上。作家弗朗西丝·菲茨杰拉德说过一句话:“磁盘和书不同,你总不能带一张软盘片上床看吧!”她观察到的这点倒是更切合这个时代。
爱书人也全神贯注,专心致志,对于地板上高高垒起的几堆书,建筑师罗伯特·A.M.斯特恩能把这些书预想成山水丘壑。他说:“角落里成堆的书不会让我不爽。我心目中的天堂是吃饭和睡觉时都有书环绕……图书馆应该是一个鼓励人与人互动的地方,可让其他人分享学习的经验,交换思想,分享迷失于其他世界的经历。”
是的,爱书人总能让人觉得惊奇。本书中有一张图片,可看到滚石乐队成员基思·理查兹埋首在他数量惊人的十八和十九世纪的小说书里。他说了句心里话:“长年累月在路上,是读书在指引着我。这么多巡回演出是很无聊的。读书可以解闷。”
爱书人也是值得相识的好心人。说起那些点燃读书藏书之情的书籍,他们总会娓娓而谈,生起思旧之情。他们仍留着儿时的第一本书。他们谈到别人朗读给自己听的书——父母、老师、图书馆馆员、邻居或者亲朋介绍他们阅读的书。人的一生,多半与我们在不同时期的藏书和读过的书籍分不开:上学时读的书,外出旅游时携带的书,教人烹饪的书,指导我们去爱去学习、为人父母、与人相处的书。我们读书以增广见闻,开阔胸襟,从而熟悉艺术和音乐,了解英雄豪侠的生平。我们读书,从而与我们想了解的错综复杂的人群和万国相连。书让人联合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