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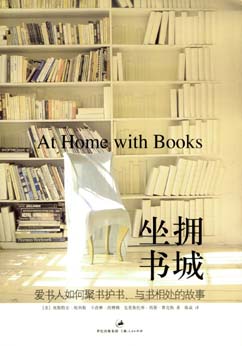 拥有稳定读者群的“书之书”,近几年来在出版界渐成规模。这种关于书的书,内容轻松有趣又饱含学识,因此也被归类为“阅读生命力”特别强的读物。2009年,这种书的大量出现更成为了“年度十大阅读热点”之一。在电子阅读的冲击下,“书之书”彰显出一些读者对传统图书的美感追求与阅读坚持。 拥有稳定读者群的“书之书”,近几年来在出版界渐成规模。这种关于书的书,内容轻松有趣又饱含学识,因此也被归类为“阅读生命力”特别强的读物。2009年,这种书的大量出现更成为了“年度十大阅读热点”之一。在电子阅读的冲击下,“书之书”彰显出一些读者对传统图书的美感追求与阅读坚持。
最近,“书之书”依然层出不穷。曾推出不少“书之书”佳作的“海上文库”丛书,在今年北京图书订货会上又一口气出版了3种典型的“书之书”,分别是陆灏的《看图识字》、张新颖的《迷恋记》和沈胜衣的《书房花木》。去年由中华书局陆续推出的精装小开本“书人书事”系列,也增加了谷林的《上水船甲集》和《上水船乙集》、严晓星的《近世古琴逸话》等3种。此外,岳麓书社也在“书之书”上“小试牛刀”,最新出品了装帧雅致的书话系列,包括杨小洲的《夜雨书窗》、止庵的《沽酌集》、谢其章的《搜书后记》,还有继续推出更多同类作品的计划。
为什么“书之书”能够形成出版、阅读热潮?这是否属于一种“小众文化”?小开本精装是否已成为“书之书”装帧的主流形式?“书之书”的兴起是不是对电子阅读是一种“抵抗”?未来的“书之书”有什么样的发展趋势?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多位出版界和读书界的专家、学者,探究“书之书”背后的“秘密”。
什么是“书之书”?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藏书家陈子善认为,关于“书之书”,不能下一个“非此即彼”的严格定义,而应该给它一个宽泛的范围。“因为书籍本身就是五花八门的,所以‘书之书’也应该是丰富多彩的。”陈子善说,“书之书”往往对关于书的事情谈得比较有趣,能够从一些别人意想不到的角度切入来讨论书,而不是理论化的书评,也不是对书内容进行严肃分析的文章,总之不是“板着面孔”的,而是有趣的。当然,“书之书”也有学术含量,但和正统的学术书籍一定是有所区别的。“‘书之书’可以讨论作者一些有趣的掌故,也可以讨论书的装帧、版式,还可以讨论书在流通的过程中发生的一些有趣故事,比如扫红的《尚书吧故事》,就以做旧书店生意的角度,讲她经手了哪些书,哪些人买走了哪些书,这里面一定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国外就有很多书店老板写的回忆录,这都可以纳入‘书之书’的范围。”在陈子善看来,书话类作品是“书之书”中比较重要的类型,比如早期唐弢、叶灵凤、阿英的一些书话作品。而现在“书之书”的范围还可以更加广泛一些,“就像写游记一样,中心都是写旅游经历,但写的方法可以有很多样,‘书之书’也如此。”
从较大的范围来看,“书之书”主要由书话类散文结集和以书为线索的小说等作品构成。在书话作家、出版人杨小洲看来,“书之书”的类型也有很多种,“有谈老版本的,有谈签名本的,有谈淘书经历的,有谈所淘之书的,有谈国外珍本的,有谈中国刻本印本的,有谈新文学的,有谈老杂志的,有谈毛边本的。”杨小洲认为,写书话的作者有很多,相比较而言,有写得很好的,比如黄裳先生,文辞及趣味之好,可称“书话翘楚”。
“书之书”为什么受欢迎?
北京万圣书园总经理刘苏里介绍,“书之书”通常都销售得比较好,比如《查令十字街》、《书店》、《如何读一本书》等“书之书”,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不是畅销书,但比一般的学术书好卖。”
山东画报出版社编辑部主任徐峙立在分析“书之书”受欢迎的原因时说,确实有很多读者喜欢了解别人尤其是文化名人在看什么书、谈论什么书,在一些读者眼里,名家名人对一本书的读法起了很大作用。“我们出版的‘书虫’系列,就有一批固定的读者追捧,还有读者一直追着收藏‘书虫’系列的‘毛边书’。”
香港文化学者、书评人梁文道告诉记者,他收集了不少“书之书”,因为他对这方面的题目特别有兴趣。“虽然中国的阅读人口不多,但是喜欢书本身的人还是有一定的数量。对于纯粹爱书的人而言,‘书之书’是很有趣的。”
杨小洲认为,“书之书”若要受到读者认可,最要紧在于趣味。“掌故逸事都是为了人文趣味而作,失去趣味,书读得再多,写出的文字也如同嚼蜡。”杨小洲说,最近他在中华书局和岳麓书社出版的两种“书之书”只求两点:一是文字好,二是有趣味。
“同样是买书日记,有的人写得比较好,有的人则写得很平淡。”陈子善认为,“书之书”的作者不能总是写一些“老生常谈”,而应该有自己的视角和判断力,这是需要长期培养锻炼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