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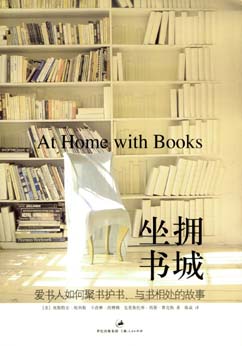 古人云“始信百城难坐拥,从今先要拜钱神”。藏书家并非都是富人,但穷人是当不了藏书家的。藏书也是一门需要技巧的行当,不是比谁的书数量多而是比谁的藏书有特色。 古人云“始信百城难坐拥,从今先要拜钱神”。藏书家并非都是富人,但穷人是当不了藏书家的。藏书也是一门需要技巧的行当,不是比谁的书数量多而是比谁的藏书有特色。
六年前,我写了“等待《坐拥书城》”,发在一张科技类报纸的读书版,仅隔了六年,我已不像当年那么热切的盼望某一本书了,许多预告得非常好的书及至到手后并非“非常好”,非常不好倒屡屡光顾,失望积多,怀疑积多,积重难返。还有一个原因,这六年我们引进了大量的关于书房及藏书的外版书,读者的眼晴有点儿挑剔有点儿疲劳了,比之六年前,现在的读者比较难伺候了。恰逢这当口,《坐拥书城》来了,来了就来了,收到书的时候我正要出趟远门,就把《坐拥书城》带上了,想着是在火车上翻翻,谁知卧席九点就熄灯了,没翻成。住进旅店才有功夫看了一半儿,主要是浏览了一遍插图,感觉图片里的书房太新潮,不够古董,尤其是选来作为封面的这张,好像就是装饰公司的招贴画,那把座椅也太急于呼应“坐拥”之意了。我的好友有此书的原版本,封面与此不同。关于书房,我写过“在伦敦雾气蒙蒙永无天日的老宅里,藏书也许是比打桥牌更有意思的消遣,浸淫着潮乎乎的冷空气,根本就不想到户外,只有随手翻着一册18世纪手工制作的‘限定本’,一篇隽永的藏书记就这么诞生了。”
《坐拥书城》初版时间是1995年,如果那年引进,我等还不看傻了。书里所展示的40位现代西洋藏书家的书房,一点儿也引不起我的嫉妒,它们像高悬的月亮,世上有几人登过月球。1980年代的《读书》杂志有那么两三年每期封三刊登一个文人的书房——确切地说就是一张书桌或一个书柜,没有全景的,也登不了全景(全景就会把其他与书房不搭界的乱物拍进去了)。1980年代住房均逼仄不堪,拥有纯粹的书房是文人之梦。比起我们低矮暗淡的书房,西方之书房犹如宫殿般富丽堂皇,有着很高很漂亮的天花板,人在书籍面前会感到自身的渺小,置身在如此华丽的书房内人更显渺小不堪。我不嫉妒,还有另一原因,我不懂他们的文字,他们书房里的珍本我一本也不眼馋,我只接受他们的藏书理念和某种技巧——虽然我们的藏书史不逊于他们,可是我们近一百多年的藏书理念远落后于人家,所以只好不断引进——像“五四”时期引入马克思列宁主义。唯一一本我们自己人写作的《书店风景》,写得还是西洋书店。《坐拥书城》中译本有作者专为中文本写的序言,这似乎很少见,此书已有几种译本,作者说:“据我所知,不是所有中国读书人的家里都有很大的地方来特设一个传统书房。”现在我周围很有几位朋友的书房很气派很专业了,这大都是这几年构建的,这几位都是收集古旧书的——我通常说的书房即指此类书房,摆了一屋子新书的房子还是房子。
我对西洋书房有兴趣,这兴趣多不在书,而在书桌,书柜的样式上,在我看来一张古董级的经过几代人使用的书桌堪与珍本等值。我们的藏书家在书房的陈设,家俱的选择上大都缺乏起码的美学常识,很不够精心,像著名收藏家马未都的书柜,居然在显赫的位置上让我看到了《辞海》、《辞源》一类大厚本工具书,虽非“焚琴煮鹤”,也是风景小煞。我看外国电影,第一遍看情节,第二遍第三遍就是只关注室内陈设了。《蝴蝶梦》里德文特夫人的书房给我印象很深,卧室的衣柜门设计独出心裁,我至今没看到第二件。《坐拥书城》有几处提到了书桌,但均未给出特写的照片。伦佐·蒙贾尔迪诺那架“仿米开朗基罗风格的书桌”简直就是一座宫殿的小模型;布拉斯有一张18世纪的书桌,我从照片上看,它是推拉式的桌子,推进去是一张长桌,拉出来即是方桌,那个黄铜大拉手隐约可见,桌上的那块斜面是怎么与桌子勾连的就猜不出来了。鲁迅有张折叠书桌瞿秋白使用过,木制书桌尽可施展木工的奇思佳构,其他材质就难比木材。菲茨杰拉德有一张长桌子靠着墙,他称此桌为“炼狱”——出版商赠阅的新书在此桌等候或被阅读或被丢弃的命运。麦克莱恩爵士的书桌被满桌的书覆盖着,他坐在桌前,桌前还有书堆,但还是有五个大拉手露了出来可知此桌之阔绰。书桌一般只能端坐在正面读书写字,这是为了节省地方,地方够大的话,还是四面可用的大书桌气派。特肯夫妇的书房原是磨坊,改造为书房后,中间搁一张19世纪的英国书桌,四面皆可坐人。书房必不可少的家俱还有书柜、书架、座椅等,我逛了20年的家俱店,没有一款书房家俱是十全十美的,倒是现在的仿古家具非常之不错,只有一点不相匹配,古典家具不大适宜搁平装书,显得不伦不类。很少有人想到期刊杂志在书房中如何安置,《坐拥书城》里有张图片,那个书架是专为几百本《国家地理》制作的,在一本杂志一公斤重与一平米房价一万元的今天,给它们安家足够伤脑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