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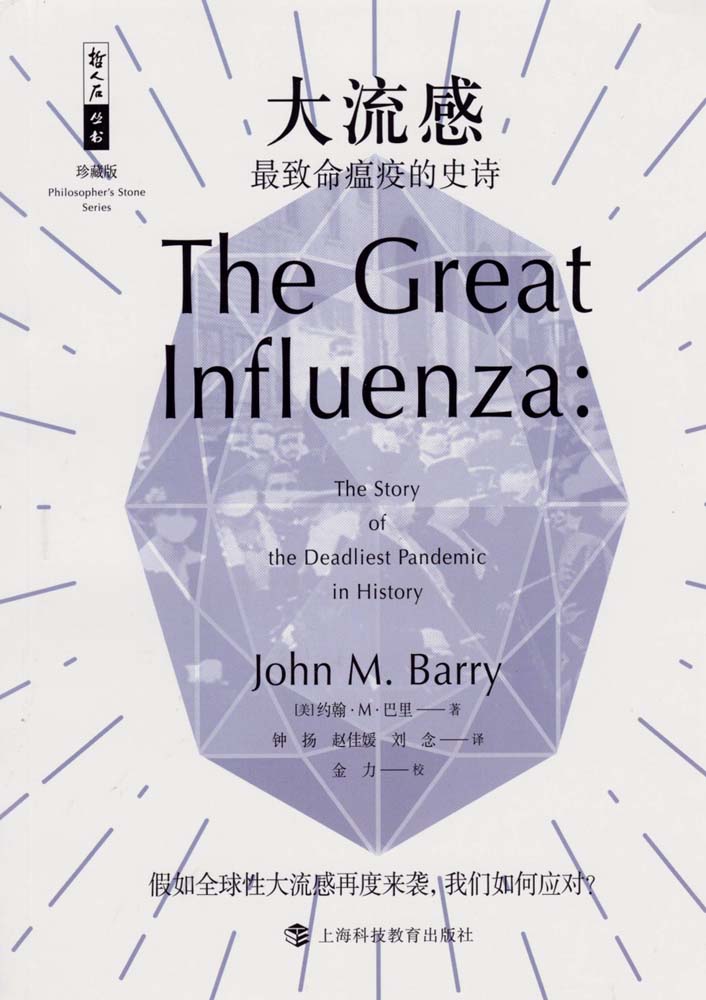 本文摘选自《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 本文摘选自《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
约翰·M·巴里 著,钟扬、赵佳媛、刘念 译,金力 校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18年7月
1918年,在门上挂一块绸布暗示家里有人去世已约定俗成。费城到处都是绸布。安娜·米拉尼回忆说:“如果死者是年轻人,便挂白绸;如果是中年人,就挂黑绸;如果是老人,就挂灰色绸布。那时我们还是孩子,总是兴奋地去找接下来是谁死了。我们盯着门看,原先挂着绸布的是不是挂上了新的,原先没挂的是不是开始挂起绸布。”
总是不断有门口新挂上绸布。“人们像苍蝇一样死掉,”克利福德·亚当斯说,“在春天花园大街上,几乎每隔一所房子就会有一扇门罩着绸布,表示他们家有人死了。”
然而,流感最可怕的一面乃是不断堆积起来的尸体。殡仪员劳病交加,筋疲力尽。他们找不到地方安置尸体。而掘墓人不是病了,就是拒绝埋葬死于流感的人。费城监狱的主管曾让犯人去挖墓穴,但不久就撤销了这项决定,因为没有健康的警卫来监管犯人。没有掘墓人,尸体便无法埋葬。殡仪员的工作区已堆满了,他们只好在礼堂里、在自己的住所中堆放棺材——许多人就住在自己和死人打交道的地方。
不久,棺材开始短缺。少数还能用的棺材猛然变得无比昂贵。多诺霍家里是开殡仪馆的,“殡仪馆外堆满了棺材,我们不得不派人看守它们,因为人们开始偷棺材……这其实和盗墓没什么两样。”
不久后,就算想偷棺材也没得偷了。阿普奇斯对棺材的奇缺记忆犹新:“一个七八岁的邻家小男孩死了,人们习以为常地用床单把他卷起来放到推车上。孩子的爸妈尖叫道:‘让我用个通心粉的盒子’[当棺材]——通心粉,那是一种意大利面食,这种盒子能装近9公斤——‘求求你们让我把他放在通心粉盒子里,不要就这样带走他……’”
据克利福德·亚当斯回忆,“成堆的尸体……堆在那儿等候埋葬……人们却没办法埋葬他们。”积压的尸体越堆越多,房内全被堆满,不得不放置到门外走廊上。
费城的太平间通常能停放36具尸体,结果那里塞了200具尸体。骇人的恶臭使人不得不开着门窗通风。那里再也容不下更多的尸体了。在家里死掉的人的尸体就停放在家里,他们死时鼻孔或嘴里总是渗出血水来。家人将冰块铺在尸体上,即便如此尸体仍会腐烂并发出恶臭。廉价公寓没有走廊,也很少有安全通道。人们把放尸体的屋子隔离起来,但锁了门并不能使人忘记门后放着什么,也无法抹去人们的恐惧。费城的住房条件比纽约还要紧张,这里大部分地区的人们没有可以隔离起来的空间。尸体被裹进床单,推到角落,通常一放就是好几天,恐怖的沉重感与时俱增。人们病重到不能做饭,没法洗漱,也无力将尸体搬下床,只能同尸体躺在同一张床上。死人被放在那里好几天,活人就同死人一起生活,因为这些尸体而感到恐惧。但也许更可怕的是,活人慢慢习惯了和死人在一起。
死者的症状非常可怕,七窍流血。有些死尸的表情极度痛苦,另一些人则是被精神错乱夺走了生命。
通常每家会有两人死掉,一家死了三口的情况也不稀奇,有的家庭遭受的打击更为沉重。
瘟疫。大街上的人都在窃窃私语谈论着这个词。这个词有一次不小心在报纸上出现了。“士气”问题、自我检查、编辑们的意图——把每一则新闻都以最积极的内容展示出来,这些都意味着没有任何报纸会再用这个词了。然而,人们根本用不着报纸去谈什么黑死病。有些尸体几乎变成了黑色,人们亲眼目睹后,就再也不轻信报纸的言论了。一名年轻的医学院学生曾被召来治疗过上百名病人,他回忆说:“紫绀达到了我闻所未闻的强烈程度。的确,关于黑死病又回来了的谣言沸沸扬扬。”报刊引用了利奥波德医生的话,听起来合情合理:“这种谣言有充分的理由……确实有许多人的身体颜色发黑,并在死后发出强烈的气味。”但他也向人们保证:“关于黑色瘟疫的断言是假的。”
他当然是正确的,但还有多少人相信报纸?即使黑死病并未来到,还是有一场瘟疫降临了,随之而来的是恐惧。
战争已经打到家里来了。
早在夏加多恩自杀之前,早在费城游行者开始沿街游行以前,流感就已经沿着国家的边境种下了病源。
9月4日,随着波士顿的三个水手——不久后这三人都死了——被送往“哈罗德沃克”号外的医院,流感到达了新奥尔良。9月7日,随着水手们从波士顿迁来,流感抵达了五大湖海军基地。接下来的几天,大西洋和墨西哥湾海岸——包括纽波特、新伦敦、诺福克、莫比尔和比劳克斯等地的港口和海军基地,也相继报告了这种新流感。1918年9月17日,弗吉尼亚州彼得斯堡的李军营周围报告有“类似流感的疾病大范围流行”。同一天,早些时候从费城出发的数百名水手到达了普吉特海湾,其中11个人是用担架从船上抬到医院的,从而把新的病毒带到了太平洋。
病毒横贯整个国家,在大西洋、墨西哥湾、太平洋、五大湖上建立了据点。它并没有立即以流行病的形式爆发,而是暗暗撒下病源的种子,随后种子开始慢慢发芽,最终怒放出绚烂的花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