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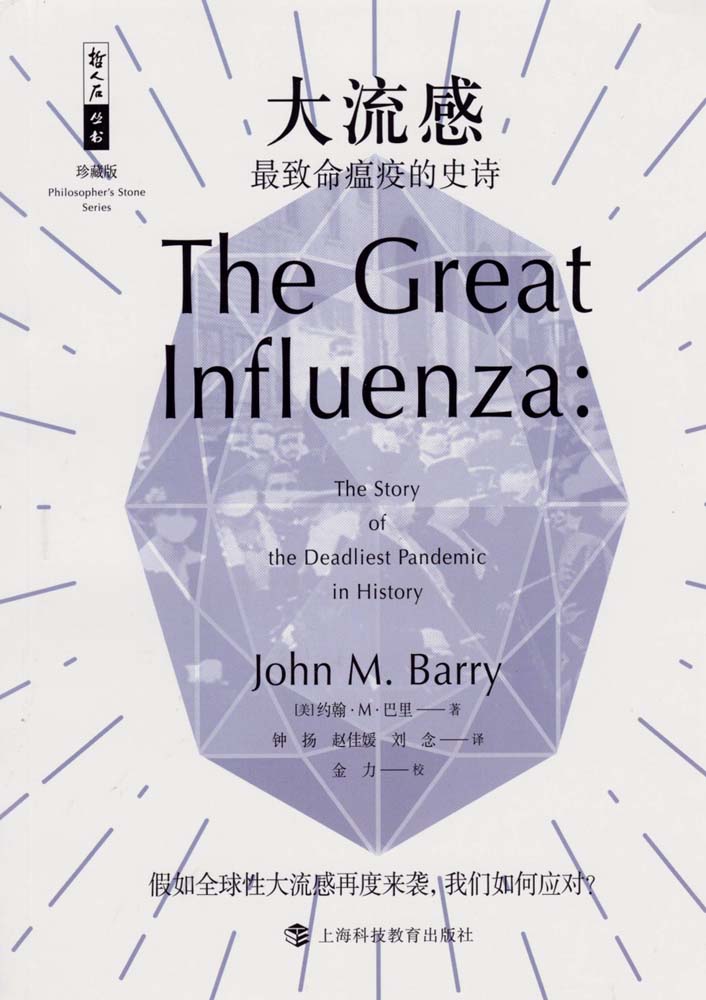 本文摘选自《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 本文摘选自《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
约翰·M·巴里 著,钟扬、赵佳媛、刘念 译,金力 校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18年7月
沃恩认为文明社会在流感威胁之下已岌岌可危。事实上,一些疾病确是依赖文明社会而存在。麻疹就是一个例子。由于患过一次麻疹通常就可终身免疫,所以在小镇中,麻疹病毒由于找不到足够的易感个体而无法存活。如果没有新的一批人感染,该病毒就会逐渐消失。流行病学家已经计算出,麻疹病毒至少需要50万在生活上有相当密切联系的非免疫人口才能继续存活下去。
流感病毒却并非如此,它不依赖于文明社会,因为禽类为其提供了天然家园。就其自身生存而言,人类的存在与否无关紧要。
大流感爆发前20年,H·G·韦尔斯出版了一本关于火星人入侵地球的小说——《星际战争》。火星人驾驶死亡飞船进军地球,令地球人节节败退。他们开始以人为食,探至骨髓深处汲取生命力。人类尽管在19世纪成就辉煌、统领世界,此时却突然变得不堪一击。没有一种人类知晓的力量,或者说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是个人拥有能阻挡这些入侵者的技术、战略、力量乃至英雄主义气概。
但在人类看似将不可避免地被灭族的当口,自然界插手了。入侵者自己也被侵入了,地球上具有传染性的病原体杀死了它们。自然作用完成了科学力所不能及的任务。
随着流感病毒的行进,自然开始发挥作用。
最初,那些作用使病毒变得更为致命。无论病毒第一次从动物宿主转移到人身上是发生在堪萨斯州或是其他什么地方,反正在人传给人的过程中病毒渐渐适应了新宿主,感染能力越来越强。1918年春天的病毒在第一波病潮时引发的症状还是温和的,到秋季第二波袭来时,病毒已摇身变成暴戾的杀戮者。
而这一旦发生,一旦病毒的传染效率接近顶峰,另外两种自然作用便会参与进来。
其中一种作用与免疫有关。当流感病毒感染过一批人后,这批人至少会对它产生一定的免疫力。被感染者不太会被同种病毒再度感染,除非发生抗原漂变。在1918年的城市或乡镇,从第一例患者出现到该地疫情结束,这个周期大致需要6—8周时间。在军营中,因为人群比较密集,该周期通常为3—4周。
那之后,仍会有个别病例继续出现,但疾病的爆发结束了,并且是戛然而止。病例统计图呈钟形曲线——峰值过后,曲线像陡峭的崖壁一般骤降,新增病例猛然下降,几近为零。以费城为例,到10月16日为止的那一周内,4597人命丧流感。疾病使城不为城,街上空无一人,关于黑死病的流言四起。然而,新增病例的数量降得如此之快,仅10天后的10月26日,关闭公共场合的禁令就撤销了。到11月11日停战时,流感几乎从费城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病毒之火燃尽了可用资源,便迅速衰竭了。
第二种作用发生于病毒内部。只有流感病毒有这种情况。从本质上讲,流感病毒的确很危险,远比人们所能想见的疼痛及发烧危险得多,但通常情况下它也不会像1918年时那样造成那么多死亡。1918年的大流感是病毒肆虐的巅峰,这在历史上其他大规模流感爆发中是前所未有的。
但1918年的病毒同所有流感病毒、所有能形成突变株的病毒一样,突变速度非常快。这里涉及一个称为“回归均值”的数学概念,即一个极端事件后接下来很可能是中庸事件。这并不是一条定律,仅仅表示一种可能性。1918年的病毒正是这样一个极端事件,任何突变都更可能使病毒的致命性变弱,而非变强。一般情况下,事态都应如此发展。所以,就在病毒几乎让文明社会屈服在它脚下之时,就在中世纪那场瘟疫造成的灾难即将重演之时,就在整个世界快要被颠覆之时,病毒开始“回归”突变,向大多数流感病毒所具的行为突变,随着时间流逝,其致命性慢慢降低。
这一现象在美军军营中初露端倪。
与此类似,第一批受到流感病毒攻击的城市都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而在同一地方的流感后期病患,其病情程度和死亡率较之最初两三周的流感患者都要低。
流行病后期受感染城市病人的死亡率也大都较低。
同样的模式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它也并非那么精准,病毒从来不按常理出牌。不过,那些后受侵袭的地方更容易被攻入。圣安东尼奥受感染人数的比例在全国最高,而死亡率却最低:总人口的53.5%患上流感,全市98%的家庭内至少有一人感染上流感,然而那里的病毒突变倾向于温和类型,因为仅有0.8%的流感患者死亡(此死亡率仍为普通流感死亡率的两倍)。孰死孰生,取决于病毒本身,而非所采取的任何治疗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