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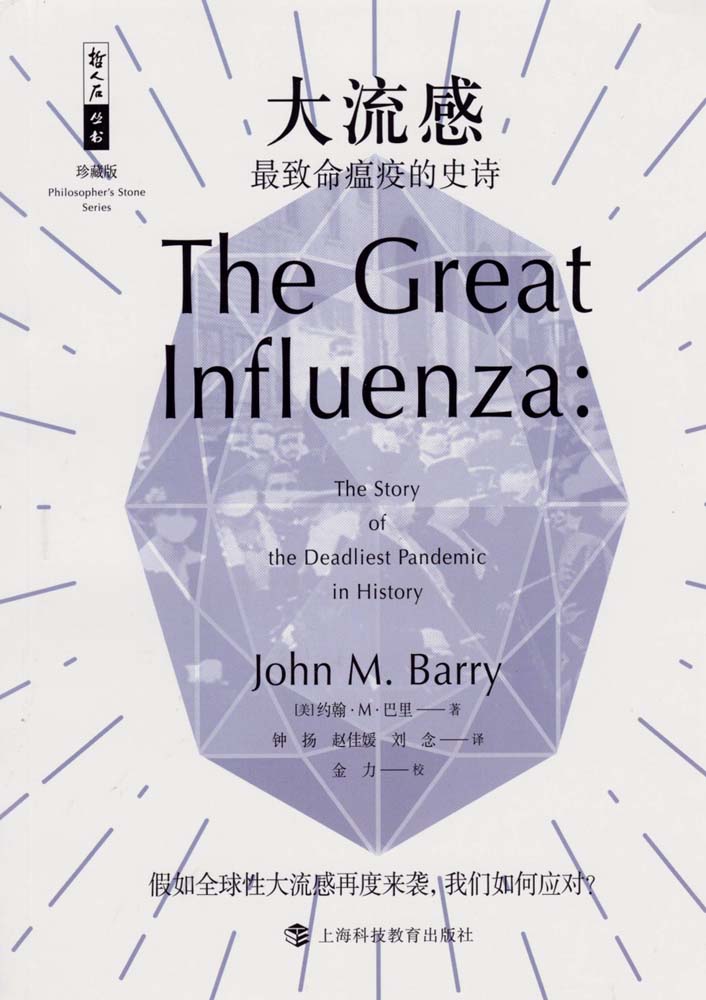 本文摘选自《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 本文摘选自《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
约翰·M·巴里 著,钟扬、赵佳媛、刘念 译,金力 校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18年7月
加缪曾写道:“适用于世上一切疾病的道理也适用于鼠疫。它也许可以使一些人思想得以提升。”
沃德博士就是人性升华者之一,当时他已经舍弃医学而去经营农场了,而他的弃医从农本也不是为了赚钱。
沃德天资聪颖,对药理学尤为感兴趣,是堪萨斯城的名医。
他已经当够了医生,而且,在给堪萨斯城北的牛仔治疗放牧所受之伤时,他对牲畜行业已有了足够的了解,于是就在战前不久,他决定买个1000多公里外的小农场,就在靠近墨西哥边境的得克萨斯州圣贝尼托附近。在往南去的漫长旅程中,他和妻子约定,对他曾行医一事决不对外吐露半个字。然而,1918年10月,流感也影响到了他。一些农场工人生了病,沃德开始为他们治疗,消息就这样悄然传开了。
几天后,他的妻子被嘈杂而陌生的声音吵醒。她走出门去,暮霭沉沉中有人影慢慢浮现,有好几百人,几乎是铺天盖地而来。他们慢慢走近,她看出他们是一些墨西哥人,几个人骑着骡子,大部分步行着,女人牵着孩子,男人带着女人,蓬头垢面,疲惫不堪,这群人身心俱伤。她大声叫喊她的丈夫,沃德出来了,站到门廊上。“我的天哪!”他叹道。
这些人什么都没有带,但他们知道他是医生,于是就来了。沃德夫妇后来告诉他们的孙女,当时就和《飘》里医院的场景一样,成排的伤者和垂死的人痛苦地躺在地上。这些人空手而来,一无所有,他们就快死了。沃德一家把巨大的水罐拿到外面烧水,用他们所有的储备来为他们提供食物,给他们治病。在靠近墨西哥边境空寂的恶劣环境中,他们没有红十字会可以求助,也没有国防委员会。他们尽其所能,当一切结束后他们回到了堪萨斯城,沃德开始重操医生旧业。
还有其他像沃德夫妇这样的男男女女——医生、护士、科学家——恪尽职守,甚至染上流感而殉职,因此而死的人数之多,使得《美国医学会杂志》每周都要数页并发,不登别的,全都是以极小字体印出的简单讣告。几百名医生牺牲了,是几百人啊!还有其他人也在鼎力相助。
但正如加缪所知的,邪恶和危机不会让所有人的人性都得以升华。危机只能让他们暴露自己,其中一些人就暴露出人性的阴暗面。
费城爆发的疾病狂潮开始席卷全国各地,被同种恐惧席卷的街道一片死寂。大部分男人和女人牺牲了,他们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只是为了他们挚爱的人:孩子、妻子、丈夫。有些人,那些只爱惜自己的人,却是抛下他们,落荒而逃。
甚至还有一些人在那儿煽动恐慌,他们相信将过错推给敌人——德国——能够对战事有所帮助,又或者他们真认为责任就在德国。多恩怪罪“乘潜艇而来的……德国特务”把流感带到了美国。“欧洲的流行病是从德国人那里先开始的,他们没理由对美国特别客气。”
美国其他地方也有人在附和。密西西比州的斯塔克维尔是密西西比丘陵地区一个拥有3000人的小镇,它坐落于锯木厂、棉花田(并不是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富饶繁密的种植园,而是一片贫瘠的土地)和密西西比农机学院(今为密西西比州立大学)附近。负责密西西比州东北部的美国公共卫生部官员帕森斯博士将斯塔克维尔作为指挥部。他不无自豪地告诉布卢说,他已经成功地让当地报纸将他编造的故事公之于众了,他说那个故事能够“帮人们形成一种合适的心态”——这种心态就是恐惧。帕森斯想制造恐惧感,他相信这能“使公众接受并执行我们的建议”。
帕森斯让地方报纸报道说:“德国佬要残杀无辜的平民……他们通过病原体散布疾病和死亡,并已经这么做了……更准确地说,传染病就是他们在法国、英国和美国的战场后方使用的武器。”布卢对此不置可否。另一个故事说:“病毒就要来了,一场流行性感冒正在传播或者被人传播(我们想知道究竟是哪种情况)”……
类似的控诉加起来足以煽动起公众的情绪,迫使公共卫生部实验室浪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去调查发动细菌战的可能媒介,如拜耳公司的阿司匹林。帕森斯的管辖范围与阿拉巴马州接壤,而那里正有一个从费城来的旅行推销员,名叫托马斯,他因被怀疑是传播流感——等同于死亡——的德国间谍而遭逮捕。后来托马斯虽被释放,但10月17日,就在费城有759人死于流感的第二天,他的尸体在一家旅馆的房间中被发现,手腕和喉咙都被割断。警方判定是自杀。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和别的地方相比,流感其实只是轻轻碰了凤凰城一下。恐慌到底还是来了。狗讲述了可怕的故事,但它们并不是用吠声讲的。有流言说狗身上携带了流感病毒,于是警察开始捕杀街上所有的狗,人们开始杀掉自家的狗,他们曾宠爱过的狗。要是他们自己下不了手,他们就把狗交给警察去杀。《公报》报道说:“照这样的非自然死亡率,凤凰城不久就会一只狗都不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