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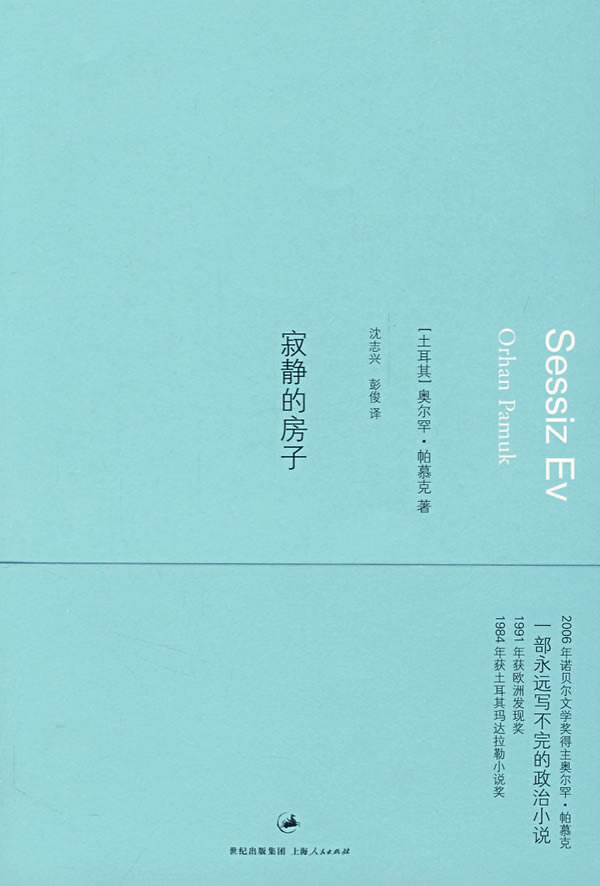 仍在生长中的作品 仍在生长中的作品
我喜欢看一个作家进步时期的作品,远胜过看其各方面都成熟后的杰作。杰作固然完美,但已经把一个有天赋的凡人进化为天才级大师的痕迹,全部抹掉或者尽力隐藏了,而青嫩时的作品,却坦然又羞耻地,带着一切印记,从中甚至可以窥见一个作家怎样思考,怎样朝着他的特质漫步或者游移,怎样具有着无限的可能,也同时连带着与此相应的多种瑕疵。然后再怎样在岁月的缓流和内心的风暴中,磨掉杂质,渐趋纯净,最终成为他自己。
《寂静的房子》对于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来说,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在这本完成于他仍然生涩的28岁的小说里,他所痴迷并在《红》中完善的多角度第一人称陈述已经成型,他对诗人式政治人物的描述,虽然远不及在《雪》中的卡那么深入,但已经展露出了轮廓,他所主要具有的气质与方式,题材与体裁,已经显露,但仍然芜杂,还带着别的大师的影响痕迹,作品中时常出现别的杰作的交响。
塞拉哈亨在被政治的漩涡甩出权力乃至正常生活的中心之后,对“唤醒整个东方”的科技的迷恋,在自己家的厨房里验证已被发现的“真理”的狂热,那情形和语调,和退出军事抗争后困守马孔多的上尉何其相似。法蒂玛面对无尽孤寂及无涯时间时的心声,依稀回响着福克纳与伍尔夫的私语。
如果说现在的奥尔罕·帕慕克已经是一位伟大的艺术炼金术士,那么写作《寂静的房子》时,他仍在修习穿墙术。
奥尔罕·帕慕克是个年轻且坦率的作家,他不惮说出自己的门径,也不惮描述自己的生长轨迹与刻下内心,他在各种访谈中说出的世界,和他所写下的世界相比,并没有什么刻意的隐藏。
也许正因为这样,他对《寂静的房子》的自我评价是“一部永远也写不完的政治小说”,这评语顺理成章地成了这部小说最醒目的标签。
其实小说写的是被甩出政治漩涡的一家人的生活。这是一群人毫无内驱力的生活。
塞拉哈亨因政见不同被驱逐出首都,举家迁往荒凉小镇,在这里怀抱重回政治与权力中心的希冀,生儿育女,但在那个混乱的社会,所有人的梦想都未能实现,这个家族住在“天堂堡垒”之中,慢慢堕入各自的黑暗命运。
塞拉哈亨的内驱力被政治的顽固和持久的贫穷消磨殆尽。他转而向“唤醒整个东方的百科全书”这样一个自我欺骗式的念头及他们家那纯朴的女佣寻找安慰。他和女佣生下两个孩子,他的作为一点点侵占着年轻妻子的尊严感,持续否定后者的意义,致使她拿起棍棒,向更弱者下手,打残废了两个小孩子。
塞拉哈亨的政治诉求结束在了放逐与醇酒之中。他儿子的政治追求也在醇酒及不断的打击中终结,他的孙辈及长寿的妻子各自逃避进自己的内心,但这是一个总体迟缓,逃避行动的内心,他们各自沉浸在自我的不幸之中,动也不肯动一下,“惟恐不小心吓跑了就在他们附近的不幸阴云”。
奶奶的阴惨、长孙的自我麻醉与向内在迷宫的放逐,次孙麦廷的如潮水般涌过又如沙滩般空虚的虚荣心,小孙子的扭曲与暴戾,长子的无尽承受与逃入小人国的隐秘梦想。这家人就是这样生活在一个混乱的世界上。
最终全书唯一的光明,单纯明亮有着无辜的坚定的倪尔君遭到了自己堂弟哈桑的粗暴毒打,并在大家迟缓的拖沓及逃避行动中,一点点延误生机,送了命。
小说最迷人的地方,还在于奥尔罕·帕慕克那种独特的多重“第一人称”叙事,他如同一个高明的术士,自由穿梭于不同的人生,窥显生命的多种形态与秘密。
他写法蒂玛面临无法度尽的长夜,那种对人生的飘忽感觉及对死亡的等待,这时候作为人本身的存在,似乎正面临无底深渊又似乎已经摊开在了世界最开阔的平面上,令人深为着迷。他对时间及记忆的感悟,在抒写同类题材的作家里面,非常有特质。
侏儒的世界、怀抱单纯空想的青年女孩的世界、沉迷与自我麻醉及陈年历史中的颓废长兄的世界、辛苦养家的劳动者、残废人的儿子哈桑那因长久的不公待遇及软弱的内心而产生暴虐妄想的不良少年的世界……
每一个人物的局限及生活,都被这个高明的术士展示出来。
但《寂静的房子》所展示的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
在充满骚动的社会里,他们对现实的无奈及对内心的退守,他们内心的迟缓,拖沓,懒惰,逃避,以及暗藏侥幸,冀望奇迹,又怀抱着明显了解奇迹永不会发生的绝望。以消极的姿态,对抗无聊且无希望的生活,这是一种妥协,也是一种放弃,是彻底的不抵抗,倪尔君死于这种内心,也死于这种绝望,死于这种毫无内驱力的生活。
这是一群没有发条的时钟小人,在摇摆的时间中,慢悠悠晃着看似随意的步子,不可阻止地走向停滞。
这不仅是人的悲剧,也是人所生存于其间的那个世界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