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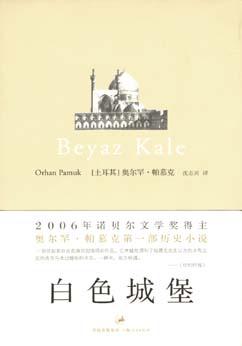 与其说《白色城堡》是向卡夫卡等文学大师致敬的“惊世之作”,倒不如说是帕慕克回望童年幻象发出的“一声叹息”。 与其说《白色城堡》是向卡夫卡等文学大师致敬的“惊世之作”,倒不如说是帕慕克回望童年幻象发出的“一声叹息”。
单看书名,小说容易让人想起卡夫卡的《城堡》,只不过在《白色城堡》中,“城堡”褪去了神秘的面纱,披上了白色的外衣。《白色城堡》中的主人公,则干脆唆使苏丹用他们发明的战争武器向城堡发出了攻击,不过这个只有在梦中才能见到的“如此美丽且难以抵达的地方”,并没有毁于炮火,反而昭示了他们失败的命运。“城堡”似乎象征了一种冥冥之中不可捉摸的命运,在《城堡》中,卡夫卡借以揭示荒谬的本质,在《白色城堡》这部小说里,帕慕克或许仅仅把它当成了一种形式。
小说讲述的故事,简单说,就是一个人和另一个自我在异域的遭遇。这种自我和他我的奇遇,显然是博尔赫斯热衷的主题,他的小说《另一个》、《博尔赫斯和我》、《两个博尔赫斯的故事》,都是对这个主题的精彩演绎。我们也很容易把它追溯到卡尔维诺的小说《分成两半的子爵》,即便在波兰导演基斯洛夫斯基《薇罗尼卡的双重生命》和日本导演岩井俊二《情书》这样的电影里,我们也不难见到类似的影子。在这些故事里,主人公免不了发出“我是谁?”的追问,也免不了做出关于存在、关于自我的探讨。然而,相近的主题、相仿的形式,帕慕克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帕慕克的“创造”不在于他讲述的故事,而在于他描述的“生活”。以往在很多小说中总是素未谋面、神交、偶遇的两个外貌神似的人,在帕慕克的小说里“生活”在了一起。不仅如此,他们终于从“镜像的隐喻”、“灵魂的影子”这些虚设的重重阻隔中破茧而出,被赋予了真实的形体,在戏剧般的共同生活中呈现出清晰生动的面目。帕慕克出神入化的想象力,又使得这种“生活”,被赋予了一种卡尔维诺所说的“轻盈”的品质。由是,当我们为《白色城堡》中变戏法一样出现的各种言论、事物、细节、故事而眼花缭乱时,我们感到的不是沉闷晦涩,而是体会到具有挑战性的阅读刺激。帕慕克避开类似幻想小说叙述中习以为常的 “陷阱”,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一个精彩的故事,更是一个奇异的“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