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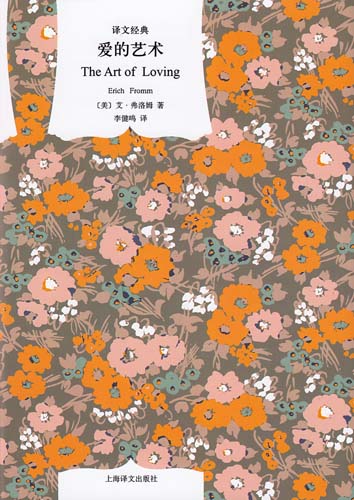 有人说这是个滥情的时代,也有人感慨“再也不能爱了”。 有人说这是个滥情的时代,也有人感慨“再也不能爱了”。
究竟什么是爱情?是瞬间喷薄的激烈,还是细水长流的温存?爱是一种能力,还是一种态度?
在这个玫瑰花与巧克力齐飞的日子里,不如我们一道翻开与爱相关的经典书籍,在阅读中谈“情”说“爱”。
爱情首先是能力,其次才是态度
《爱的艺术》
[美]艾里希·弗洛姆 著 李健鸣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再也没有比爱情更容易的了——这一看法尽管一再被证实是错误的;但至今还占主导地位。再也找不出一种行为或一项行动像爱情那样以如此巨大的希望开始,又以如此高比例的失败而告终。
“一无所知的人什么都不爱。一无所能的人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懂的人是毫无价值的。但是懂得很多的人,却能爱,有见识,有眼光……对一件事了解得越深,爱的程度也越深。”看完德裔美籍心理学家和哲学家艾里希·弗洛姆的这本著名书作后,你就会深深理解德国医学家、哲学家巴拉塞尔士的这句论断。
这是一本可以轻松阅读又能发人深思的书。
弗洛姆认为,爱情首先是一种能力,其次才是一种态度,这种能力和态度更大程度上和你爱的对象没有关系,它就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如果没有爱的能力作为前提,那么一个人将无法得到爱情,至少无法得到他(她)理想中的爱情。其次,爱情才是和善良、责任心、谦恭等词汇联系在一起的态度问题。
所以,爱并不是一种与人的成熟程度无关的感情,而是可以通过训练自己的纪律、集中和耐心学到的一门艺术。
这本《爱的艺术》自1956年出版至今已被翻译成32种文字,在全世界畅销不衰,被誉为当代爱的艺术理论专著中最著名的作品。
如果你觉得光看作者的论述不够带劲,还想顺便“八卦”一下作者的成长史和感情史,那么译文社的这个版本正合适,里面特别收录了弗洛姆学术助手撰写的纪念文章 《弗洛姆生命中的爱》。
拥有幸福回忆的人,才是富翁
《纯真博物馆》
[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 著 陈竹冰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每个聪明人都知道人生是美好的,人生的目的是获得幸福。但最后只有傻瓜们才会幸福。我们将如何来解释这个问题?
在土耳其,真的有一座“纯真博物馆”。
在小说《纯真博物馆》里,富家公子凯末尔深爱芙颂,却错失这段姻缘,他一路追随芙颂,并悉数收集起她用过的盐瓶、小狗摆设、顶针、笔、发卡、烟灰缸、耳坠、纸牌……这些在小说中被放入“纯真博物馆”的物件,也被一一陈列在伊斯坦布尔的这座博物馆中,它忠实再现了小说和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上世纪50年代至2000年半个世纪间的生活。
这部小说发表于2006年作者奥尔罕·帕慕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就在小说出版的同时,帕慕克将100多万欧元的诺贝尔文学奖奖金悉数投入,开始修建这座私人博物馆,至2012年建成开馆。在世界各地各个版本的《纯真博物馆》中,都附赠了一张免费参观门票。
这样一座琐碎的博物馆,这样一个杂乱的爱情故事,究竟要告诉人们什么?
我只念一段无关“剧透”的结尾给你听——凯末尔吻了一下芙颂的照片,带着胜利的喜悦说:“让所有人知道,我的一生过得很幸福。”
的确,人生最后留下的只有回忆,而拥有幸福回忆的人,才是富翁。
练就爱情中必不可缺的执著
《恋人絮语——一个解构主义的文本》
[法]罗兰·巴特 著 汪耀进 武佩荣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佛教公案:“师父将弟子头按入水中良久,泛沫渐少;师父遂将弟子拽起,复其元气,曰:汝求真谛如空气时,便知何为真谛矣。”
不见对方,就像我的头被按入水里一样滋味;我快要溺死了,呼吸不济了,经过这种窒息,我才重新认识我要寻求的“真谛”,并练就了爱情中必不可缺的执著。
最后推荐的这本书,是一部无法用传统体裁定性的奇书。
罗兰·巴特是一位思想的饕餮者,他在书中尝试了一种高度神经质的“发散性”行文,恍如万花筒;巴特撷取出恋爱体验的五彩碎片,在他思辨的反光镜折射下,出现扑朔迷离的排列组合。
初看此书,或许会感觉眩晕,但深入下去就会明白,巴特以这迷宫般的文体揭示:恋人的絮语只不过是诸般感受,几段思绪,剪不断,理还乱。
这本书中没有小说般高潮迭起,但请相信,那些聪明的句子、从容而端庄的戏谑,饱和而不掺水的喃喃自语,一定能激起阅读者诸多关于爱情的灵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