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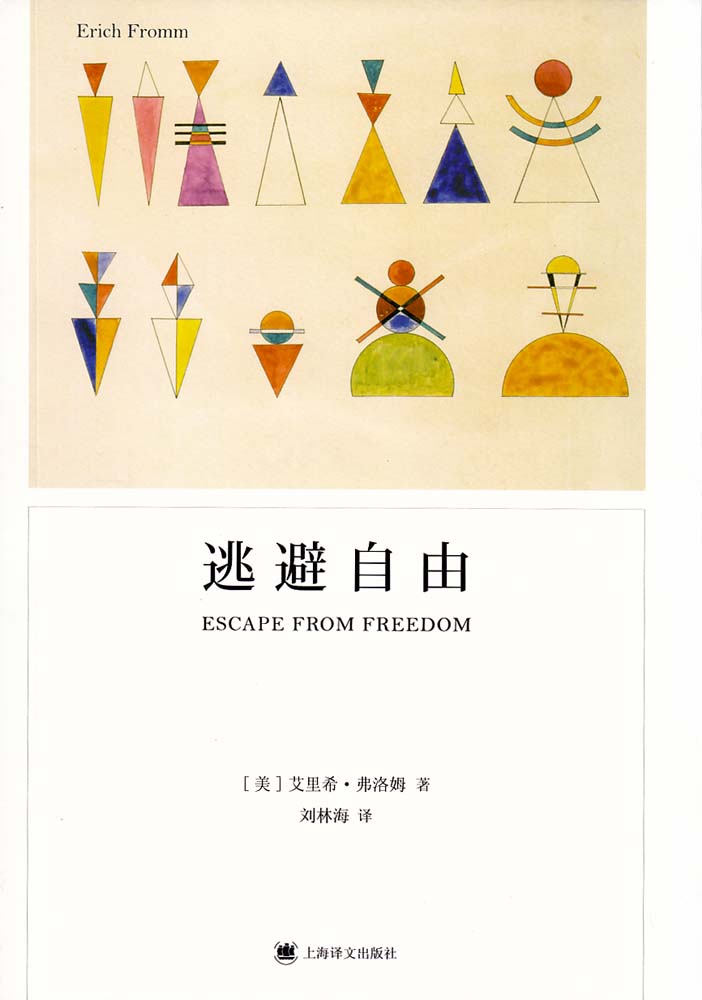 传统信念认为,现代民主制度把个人从所有外在束缚中解放出来,实现了真正的个人主义。我们不屈服于任何外在权威,我们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与感情,并想当然地认为这个自由几乎自动地保证了我们的个性。然而,表达我们思想的权利,只有在我们能够有自己的思想时才有意义。 传统信念认为,现代民主制度把个人从所有外在束缚中解放出来,实现了真正的个人主义。我们不屈服于任何外在权威,我们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与感情,并想当然地认为这个自由几乎自动地保证了我们的个性。然而,表达我们思想的权利,只有在我们能够有自己的思想时才有意义。
在《逃避自由》中,弗洛姆指出,自由给现代人带来的两方面影响,它使个人从权威中独立出来,一如离开母体的婴儿,同时这种独立又带来了孤独、焦虑和恐惧。这种无能为力感会让人产生两种逃避方式:一是权威主义性格(集施虐-受虐于一身的性格,如德国纳粹时期服从于希特勒政权的下层中产阶级)的逃避机制,另一种是孤立的个人变成机器人,失去自我的同时强迫性趋同,但又在主观意识上认为自己是“自由的”,“只服从自我”。
要研究我们的文化是怎样促成这种趋同趋势的,我只能举几个突出的例子。自发感觉及真个性的发展很早就受到压抑,实际上,从最早对儿童的训练培养时起就开始了。即便教育的真正目的在于促进儿童的内在独立和个性,在于促进其成长与完善,然而,在我们的文化中,教育的结果常常却是扼杀了自发性,外加的感觉、思想和愿望取代了原始的心理活动(请注意我所谓的“原始的”,并非指别人以前从未想到过的思想观念,而是指它生发于个人,是他自己活动的结果)。
随便举个例子来说吧!最早要压抑的感觉之一便是敌视和厌恶。起初,许多儿童由于与阻碍他们发展的周围世界发生冲突,都有一定程度的敌视和叛逆倾向,但由于他们势单力孤,便不得不常常屈服。教育过程的根本目的之一便是除掉这种敌对反应。人们采用的方式各异,从恐吓和惩罚,把儿童吓怕,到巧妙的哄骗或“耐心解释”,把儿童弄糊涂,不一而足。儿童开始放弃表达自己的感觉,并最终放弃了感觉本身。
此外,人们还教育他不要理会他人的敌视与不诚实,要压抑自己的这种意识。但有时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儿童有注意此类消极品质的能力,但这种反应很快就受到打击;儿童不久便达到了一般成年人的“成熟”程度,并丧失了辨别好人与坏人的能力,只要坏人不在光天化日之下为非作歹。
另一方面,在早期的教育中,人们教导儿童要有根本不是“他的”感觉,要特别喜欢人,要与人为善,要微笑待人。教育没达到的目的常常在后来的生活中由社会压力来完成。如果你不面带微笑,别人就会说你缺乏“令人愉快的人格”。友好、欢愉及微笑能够表达的所有东西,都像电开关一样,成了自动的反应。
毫无疑问,在很多场合下,人们清楚这仅仅是一种姿态;然而,在大多数场合下,他失去了这种意识,并失去了辨别伪感觉与自发友善的能力。直接受到压抑的不仅仅是敌视,被外加的虚假友善扼杀的也不仅仅是友善。大量自发的情感受到了压抑,并被伪情感取而代之。
总的来说,在我们的社会里,情感是大受其挫的。当然,所有创造性思想及其他创造活动无疑是与情感密不可分的,但不带情感去思想和生活已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理想。“有情感”已成为不健全、不正常的同义词。个人接受了这个标准,变得异常软弱,他的思想贫乏,平淡无奇。
另一方面,由于情感并不能完全被扼杀掉,它们必须完全脱离人格的思想而存在。结果,电影和流行歌曲把廉价、虚假的多愁善感填塞给数百万患情感饥渴症的顾客们。
另外,需要专门指出一种情感禁忌——悲剧感,因为对它的压抑深深触动了人格的根基。人的基本特征之一便是死亡意识及生命悲剧面的意识。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一套应付死亡问题的办法。
我们发现,在个体化发展程度较高的文化中,人们是根据文化的社会及心理结构来对待死亡问题的。希腊人强调生,认为死亡不过是生的一种朦胧凄惨的继续。埃及人寄希望于人的肉体不灭的信仰。犹太人承认死亡现实,因而能用人类最终在这个世界上达到的幸福正义国度之幻想来调和个人生命的毁灭之思想。基督教把死亡变成非真实的东西,并力图安慰不幸福的个人,向他们许诺来生。
而我们这个时代简单地否认死亡,并没把它作为生命的一个基本方面。不但不把死亡意识和苦难作为生命的强大动力之一,使它成为人类团结一致的基础,成为一种经历,没有它人就无法体会到欢乐和热情的强度和深度;相反,个人却被迫压抑它。但是,压抑总是如此,它虽让被压抑的因素从视野中消失了,但它仍然存在。因此,恐惧死亡便成了我们中间的非法存在物。它成了人生其他经历平淡无奇的原因之一,成了生活不稳定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