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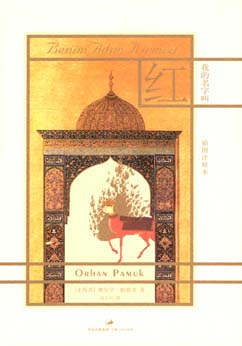 “奥斯曼帝国瓦解后,世界几乎遗忘了伊斯坦布尔的存在……她对我而言一直是个废墟之城,充满帝国斜阳的忧伤。我一生不是对抗这种忧伤,就是(跟每个伊斯坦布尔人一样)让她成为自己的忧伤。” “奥斯曼帝国瓦解后,世界几乎遗忘了伊斯坦布尔的存在……她对我而言一直是个废墟之城,充满帝国斜阳的忧伤。我一生不是对抗这种忧伤,就是(跟每个伊斯坦布尔人一样)让她成为自己的忧伤。”
一、奥斯曼苏丹与土耳其的迷失
奥尔罕·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中如此谈论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以及土耳其这个国家的衰落。毫无疑问的是,他对这样的衰落,感到极度的失望和痛苦。事实上,令帕慕克失望的不仅仅是慢慢坠落到马尔马拉海中的那一抹“帝国斜阳”。土耳其的困境更在于它在东西方的夹缝当中,在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挤压中,在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迷失了自己的方向。
与伊斯兰世界出现离心力,事实上早在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的共和国建立之前,就已经开始发生了。在伊斯坦布尔的城市变迁中,西方化的痕迹并不是以独立大街或者贝伊奥卢为开端的,而是在苏丹的宫廷里。我相信每一个游客走进紧贴着博斯布鲁斯海峡的那座多玛巴切宫(新皇宫)时,都会对宫廷内部奢华的洛可可风感到震撼。
在这座新皇宫里的游览,是一种极为绝妙的体验。同老皇宫一样,新皇宫也分为前庭与后宫。前庭是苏丹办公、起居与举行礼仪的场所。鳞次栉比的房间和走廊向迷宫一样在巨大的盒子般的皇宫中纠缠蔓延。在一位类似政府代言人般一本正经的导游陪同下,游客在偌大的皇宫中缓缓而行,这时的节奏犹如交响曲的慢板一样悠扬。大家醉心于宫殿细节处的精致,暗暗感叹却还能压抑住内心的荡漾;然而当前庭的游览结束后,导游带领大家进入中央大厅时,就仿佛整首曲子陡然达到了一个巅峰:辽阔的穹顶高高在上,各种奢华繁复的装饰遍布于整个大厅的四处。或者,同西方那些著名的宫殿相对照,多玛巴切宫带有浓重的“抄袭”味道,但是这种不厌其烦地奢华调子,也让人能够感到帝国晚期的几位苏丹在品味上多么强烈地对西方心向往之。
当然,还有链接加拉太桥和贝伊奥卢的那条名为“Tunel”的地铁,开通于1875年,是世界第二古老的地铁。建造这条地铁的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一世的身上,似乎有光绪皇帝的影子。在他的任上,阿齐兹设立大学、创立法典,开始真正理智地与西方列强展开外交。尽管最后他依旧走上了专制的道路,我们却已经能从帝国的统治中触摸到西方化的影响。
然而,正是从这时起,在加拉太桥两端的老城区和新城区之间,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东方就这样被不经意地划上了一条属于历史心理上的“沟壑”。
二、帕慕克与埃尔多安
苏丹制废除后,凯末尔在土耳其宣布实施彻底的世俗化,从此民族主义取代“安拉”,成为土耳其人的新“信仰”。然而,同伊斯兰教一样,民族主义同样没能阻挡土耳其,特别是地理位置处于欧洲的伊斯坦布尔在心理和文化上加速向西方前进。在帝国倾圮的同时,西方文明的“洪水猛兽”没有了宗教的防波堤,更是肆无忌惮地席卷着进入到了这个国家。
于是,我们今天在金角湾的北边,可以看到一个颇具欧洲味道的贝伊奥卢,而距离贝伊奥卢的商业中心塔克辛广场不远的地方,则是伊斯坦布尔的时尚中心——尼尚塔石。帕慕克从小就生活在尼尚塔石的一座老公寓楼(帕慕克公寓)。在帕慕克的作品里,那座公寓楼、尼尚塔石和贝伊奥卢,也成为曝光率最高的地名。
从近代时期开始,西方的各种文化渐次在这个区域中落地生根,布尔乔亚和波西米亚的小资情调,激进的马克思主义,正统西方的天主教,乃至于当下席卷全球的各种时尚文化。所以,当我们步行在独立大道上时,可以看到土耳其共产党的总部,还有伊斯坦布尔最大的天主堂——圣安托尼奥(San Antonio)教堂,前任教宗若望二十三世(1958-1963年在位,开创天主教中新时代)曾在布道10年。这一切成为了滋养“帕慕克们”的养料。所以,当2012年,帕慕克的那座“纯真博物馆”开张后,人们也就不会惊讶地发现,这完全是一座展现装置艺术的西方式博物馆。
然而,贝伊奥卢和尼尚塔石的崛起并没有能够填平当初的那条“沟壑”,它们反而与多玛巴切宫一起加深了那道“沟壑”。这条“沟壑”的存在,让情感上对西方文化亲近的“帕慕克们”备受折磨。世俗化没能解决他们心理上对东西方的矛盾心态。无法摆脱土耳其身份的他们,期待着世俗化的土耳其也能成为一个“欧洲国家”,以使他们在伊斯坦布尔旧街老巷中漫步时,能体会到与在布拉格、巴黎或是伦敦的街头一样的感觉。然而,他们却突然发现,阿塔图尔克主义下的土耳其包含的民族主义,成为了这种转型的新障碍。这么看来,“帕慕克们”急着承认“亚美尼亚大屠杀”,恐怕也是在文化矛盾的心态下,对传统产生的一种逆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