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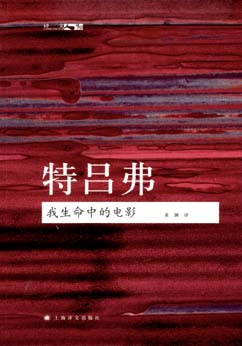 就电影史而言,特吕弗是不多的拥有多种身份的电影人之一。首先,特吕弗是一个影迷,甚至是一个有些狂热的影迷;然后,他是一个影评人,虽然他自己说他喜欢跟大多数观众或影评人对着干,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总是站在被嘘的那些人一边,而我反对的总是嘘人的那些人;而且,别人转身离开的地方,常常会是我观影时的喜悦开始之处。”但实际上,他为之唱赞歌的绝大多数电影均已成为电影史公认的经典。就其作为一位影评家而言,他有时也很偏激,特别是他刚刚开始写影评的时候,在他那篇著名的《法国电影的某种倾向》中,对当时的法国影坛展开了猛烈的攻击,这篇文章也因此既是针对当时法国主流电影的檄文,也是向他们下的宣战书,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新浪潮”的宣言,或者说是“新浪潮”的预告片。但在时隔二十多年后,这位“法国电影的破坏者”在他对电影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体会后,反而多了一份宽容,而且,这宽容也并非降低了评价标准、放弃了原则的认同,而是源于自己的经验和教训后的理解;特吕弗的第三个身份当然是导演了,不管他当初是出于对电影的热爱,还是为了驳斥“光会说不会练”的无理批评(实践家自以为对评论家最厉害的反击就是“你也来一个试试”),或者是他自己手痒得很,特吕弗以“捣蛋鬼”(他的第一部短片名)的姿态拿起了导筒,可出乎其意料的是,导演的身份使他失去了只是作为一个忠实的影迷所有的那种自由和激情,仍以他自己的话说:“我已经失去了电影迷的宽阔胸怀,变得如此傲慢和自满,有时连自己都觉得尴尬和困惑。”但是,这个世界少了一个顶级影迷,却多了一位大师级的导演。幸运的是我们,遗憾的是特吕弗。 就电影史而言,特吕弗是不多的拥有多种身份的电影人之一。首先,特吕弗是一个影迷,甚至是一个有些狂热的影迷;然后,他是一个影评人,虽然他自己说他喜欢跟大多数观众或影评人对着干,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总是站在被嘘的那些人一边,而我反对的总是嘘人的那些人;而且,别人转身离开的地方,常常会是我观影时的喜悦开始之处。”但实际上,他为之唱赞歌的绝大多数电影均已成为电影史公认的经典。就其作为一位影评家而言,他有时也很偏激,特别是他刚刚开始写影评的时候,在他那篇著名的《法国电影的某种倾向》中,对当时的法国影坛展开了猛烈的攻击,这篇文章也因此既是针对当时法国主流电影的檄文,也是向他们下的宣战书,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新浪潮”的宣言,或者说是“新浪潮”的预告片。但在时隔二十多年后,这位“法国电影的破坏者”在他对电影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体会后,反而多了一份宽容,而且,这宽容也并非降低了评价标准、放弃了原则的认同,而是源于自己的经验和教训后的理解;特吕弗的第三个身份当然是导演了,不管他当初是出于对电影的热爱,还是为了驳斥“光会说不会练”的无理批评(实践家自以为对评论家最厉害的反击就是“你也来一个试试”),或者是他自己手痒得很,特吕弗以“捣蛋鬼”(他的第一部短片名)的姿态拿起了导筒,可出乎其意料的是,导演的身份使他失去了只是作为一个忠实的影迷所有的那种自由和激情,仍以他自己的话说:“我已经失去了电影迷的宽阔胸怀,变得如此傲慢和自满,有时连自己都觉得尴尬和困惑。”但是,这个世界少了一个顶级影迷,却多了一位大师级的导演。幸运的是我们,遗憾的是特吕弗。
特吕弗似乎就是为电影而生。既如此,他也就有责任教会我们怎么看电影。
这个话一定使很多人看着不舒服。谁不会看电影!也许在所有的艺术门类中,看电影是最不需要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就如特吕弗所言,任何一个“导演必须接受这样的事实,他的作品很可能被某个连茂瑙(Friedrich WilhelmMurnau)的电影都没看过的人评头论足”,影评人尚且可以如此,一般的观众就更不需要电影史的知识和电影理论的概念了。然而,一样的看却有不一样的境界,就如特吕弗将电影导演分为“令电影前进”与“令观众前进”的一样,我们也可以对观众进行分类,譬如可以分为一般观众、影迷、超级影迷,或者普通观众、有一定艺术经验的观众和电影专业的观众,还可以根据对电影的不同需求,或进影院的动力、动机来分,因此就有纯粹娱乐性的观众,这一类观众要求的大概多半是黑暗中的快乐满足,或者一种强烈的感官刺激,以此暂时地遗忘白昼的紧张、焦虑等;当然也可以是一次消费行为,所得自然也就是消费的快乐,既为消费,也就必然有了消费行为所有的特征,诸如广告的诱引、符号化的满足等等;还可以为打发无以消遣的时间提供方便,以时间消遣时间;或作为感情生活(特别是爱情)的一种重要形式和内容,以感情增进感情。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所以,虽同样是看,却尽有各不相同的目的、方法,而因目的和方法的不同,收获也便不同。既然杰出的导演能够“令观众前进”,也就需要观众的配合,观众得抓住那些可以帮助他/她前进的东西,否则所谓“前进”不过是空幻的假设。当然,这其中必须将坚定的不愿随导演前进的观众排除在外。树林子大,什么鸟儿都有。现实中绝少不了专好抬杠的人,他/她进电影院的目的就是要属于自己的乐趣,而他/她的乐趣也就是坐在角落里,固守着自己的立场,一个人自得其乐,甚至坏笑。所以,从特吕弗对导演的分类,我们可以将观众分为愿意随导演指给我们的方向前进的和不愿意前进的两种。那么,我现在可以说,特吕弗的这本书是奉献给前者的。
有意思的是,特吕弗的这一说法还带出了另一个问题,无论是令电影前进,还是令观众前进,总还是前进,除此之外就一定有全无作为的导演,特吕弗在这本书里没有提及,或许他猛烈抨击的那些导演就属于这一类,然而,事实似乎并不尽然。随手翻近日从旧书店淘来的几期《电影艺术译丛》,其中就有特吕弗崇敬的罗西里尼关于电影的一些断片。罗西里尼在1961年就说过这样的话:“真正的艺术要同文化副产品竞争,严肃的思想要同商业化思想作斗争,胜利却总是同属一方:庸俗不堪的产品轻而易举地战胜更为严肃的产品,因为前者更易为人理解,也容易取悦于人。”这真的是令人难堪的事实。可也许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特吕弗的这本书就更有其意义和价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