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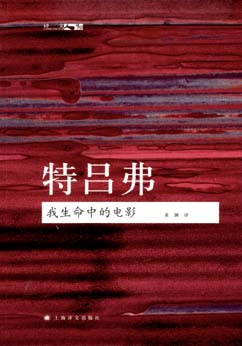 弗朗索瓦·特吕弗,是法国新浪潮的领军人物,也是电影史上最重要的导演之一。正如《纽约时报》所说,他是“一位安静的革命者,以传统的方式拍摄最不传统的电影”。 弗朗索瓦·特吕弗,是法国新浪潮的领军人物,也是电影史上最重要的导演之一。正如《纽约时报》所说,他是“一位安静的革命者,以传统的方式拍摄最不传统的电影”。
书中分为六个部分:“大秘密”、“有声片时代:美国人”、“有声片时代:法国人”、“为日本电影喝彩 、一些局外人”、“我在新浪潮的朋友们”。特吕弗笔下那些电影大师的名字就像天上的群星缭绕在他的周围,他描述了这些大师如何默片时代入行,在有声片时代继续创作的导演,以及他们身上的特别之处,读来感人肺腑。另外,书中还收录了弗朗索瓦·特吕弗亲自挑选的一些影评。特吕弗以自己对电影的巨大热情,写下了对电影的独特见解,堪称是一部电影发展史。在这部书里,能看到特吕弗如何从一个犀利乃至有些刻薄的影评人,转变成一个成熟但又不拘泥于传统条条框框的导演。同时,还能体会到他和新浪潮一代在电影发展史中的历史推动作用。
卓别林:最“边缘”的一个
在有声片诞生前的那几年,全世界的作家和知识分子都对电影态度冷淡,甚至可以说是轻蔑,因为他们都把电影看作是流行的娱乐方式,至多也就是一种小门类的艺术形式。但是,他们对一个人却另眼相看:查理·卓别林;这样的偏爱自然会令格里菲斯、斯特劳亨、基顿的拥护者感到不快。这场争吵或许会围绕电影究竟是否算是艺术而展开,但对观众来说,他们从来不曾提出这样的问题,知识分子间的争论也丝毫不会影响到他们。观众的热情——很难想像当初的这种热情放到现在会是什么规模,我们可以把贝隆夫人在阿根廷受顶礼膜拜的程度放大到全球范围内来看——令卓别林成为1920年全世界知名度最高的人。
查理·卓别林自小被酒鬼父亲抛弃,童年时一直因目睹母亲被送进疯人院的惨状而感到痛苦,自己也有过被警察抓走的经历。正如他在回忆录中写的,那时候的他是个抱着肯辛顿路墙根的九岁流浪儿,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关于这一点的描述和评论已经很多了,我之所以再次提起,是因为大家说了那么多,反而可能会令他生活的本质被忽视,我们真的应该注意一下,在极度凄惨的生活中也孕育着巨大的爆发力。在他为基斯顿公司拍摄的追逐电影中,卓别林比他那些剧团出身的同行们跑得都要更快更远,因为,即便他并非是惟一描述过饥饿的电影人,也仍是在这方面惟一有过亲身经历的导演。这也是当他的电影在1914年开始流通后,全世界的观众能从中感受到的。
卓别林的母亲发了疯, 他自己几乎完全与周围人疏远,靠着他表演哑剧的天赋,才能从这种疏离中逃脱出来,而这一天赋便来自于他的母亲。在最近几年,有人对在孤独环境、道德或身体痛苦中成长的儿童,进行了认真研究。专家们将自闭症描述为一种防御机制。巴赞解释说查理并非反社会而是无社会意识,但是他渴望进入社会。巴赞用同康纳几乎一样的话语,给那些精神分裂症的孩子和自闭症的孩子下了定义:“精神分裂症的孩子尝试离开自己曾经属于的那个世界,以解决自己的问题;而自闭症的孩子会逐渐与之妥协,只与这个他从一开始就是局外人的世界做最谨慎的接触。”
按照今天的说法,查理会是边缘人中最“边缘”的一个。当他成为全世界最出名和最富有的艺术家后,他因为年龄或谦逊的性格,或者可能是出于逻辑,而感到必须要放弃自己的流浪汉角色,但他也明白,“安定”的角色他也没法演。他必须改变有关自己的神话,但是又必须保持神话感。于是他准备扮演拿破仑,之后还有基督,然后又放弃了这些计划,转而拍摄了《大独裁者》、《凡尔杜先生》和《纽约之王》,通过《舞台春秋》中的卡尔贝罗,他让一个穷困潦倒的小丑询问剧团的经理:“要不我换个假名字来继续我的事业?”
卓别林对电影的控制力和影响力长达五十年,我们可以在《游戏规则》中的朱利安·卡雷特的身后清楚地认出他的身影来,正如我们可以在阿尔希巴尔多·德·拉·克鲁兹的背后看见亨利·凡尔杜,或如我们可以在《大独裁者》中小个子犹太人理发师看着自己房子起火的二十六年后,看见他站在米洛斯·福尔曼的《消防员的舞会》中的老波兰人身后。
奥弗斯:为演员而牺牲技术
世界上有两种导演: 一种说“拍部电影非常难”,另一种说“那很容易,你只需要把你想到的任何东西拍出来就行了,拍的时候好好享受”。马克斯·奥弗斯属于第二种,但是因为相比起谈论自己,他更喜欢谈论歌德和莫扎特,他的创作意图一直都很神秘,他的风格也没能被人很好地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