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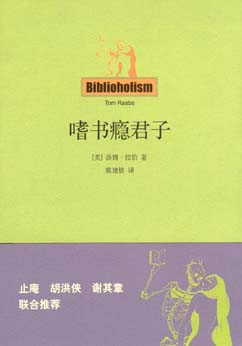 去年夏天某日,在北京城南报国寺有个约会,事先我约了止庵先生一道去,正好他没来过这古寺就答应来。报国寺里有个文化收藏品市场(以卖买古旧书为大宗),十年历史了,名气仅低于享誉全国的潘家园旧货市场。这天的约会,原本就六七个书圈里的熟朋友外加山东某报文化版的编辑,到了中午聚饭的时候,局面失控,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就是他的朋友就是大家的不分彼此,一个中等包间一张圆桌居然挤下了近二十口男男女女,央视某文化频道的两位不知什么时候也上座了。这些人我当然都了解,在藏书圈里玩了这么多年,浮出水面的都知道我,而止庵先生瞧着这帮人眼生,我跟他开玩笑,这不是你熟悉的读书圈,将就点吧,其实我们有共同话题——同为天涯爱书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只不过今天这伙子人侧重于收集古旧书,你呢,重于读而对版本不太讲究。散席之后,我问止庵有何评论,他回了八个字“高者近儒,低者近丐”,我说你骂人不带脏字,把我的朋友全否了,哪来的高者?后一句才是你的真实印象。虽然我一直警觉读书界对藏书圈(界比圈高)的偏见,不成想就是这码事——藏书圈的印象分历来不高,在旁人眼中,这是一帮不可理喻的家伙,神神叨叨,不着四六,总以为天底下唯有藏书是最要紧的事情,谁要是说他一句他的书不好,如数家珍的脸即刻就是晚娘之脸了。所以,我有责任把嗜书者分为两类,一类“嗜读书”,一类“嗜藏书”,井水不犯河水,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只有极个别天才,有能力平衡嗜读与嗜藏的辩证与统一,平庸之辈顾好一头即手忙脚乱。《嗜书瘾君子》这本书,我只看书名就猜到是谈“嗜藏书”者的,至少多一半的笔墨落在“藏”上而非劝君多读书,及至把全书阅过,先前的判断基本靠谱,虽然是外国人写作的,许多情况亦很符合我们的国情,移情换景,恰似量身定做,到底是天下爱书一家人,且看这一段人家说的话——“君乃寰宇大作家,只要书名页上所有作家,只消一眼便知其等级高低,版本种种了然于胸,其看重珍视精刊佳椠,犹胜对待维吉尔与赫拉斯,屡屡赞叹用纸如何精致,频频称颂藏家何等用心勤勉,每见秀雅铅字,便情不自禁满心开怀,仿佛如此这般,即已完成扎实学问,增进大量识见”(约瑟夫·阿迪生《汤姆·弗利欧行谊》)。藏家为读家诟病由来已久,其最大一宗罪即“只藏不读,只藏不用”,还有一潜台词“只藏不读也罢了,最看不惯那厮拿着所谓珍本满世界招摇”。而我们这里的一流藏书家说得更极端,说这话的是周越然(1885~1962)——“对于这种读书不考究版本的人,我可设一比喻。翻刻本或影印本,好比寡妇。至于随便石印本或排印的本子,简直是下贱的‘野鸡’。青年人娶妻,总希望一个好人家的女儿,不愿意与寡妇结识,或与野鸡谈恋爱的,所以真能读书者,必求精善的本子。”(“版本”原载1934年《太白》创刊号)如此伤众的言论搁今天哪还不招来如雨般砖头,当年却波澜不惊,只有两篇响应,宋云彬一篇(“也谈版本”刊《太白》),名气现在比周越然高得多的藏书家阿英一篇(“版本小言”收《夜航集》),这两篇均细雨和风,一丁点儿急赤白脸也没有,我分析,这与教养关系不大,以上世纪三十年代论战风气,什么难听的话说不出口,何以偏偏对周越然宽容?鄙意当时的嗜书如命者只是很小很小的一小撮,更多的群体首要考虑的是生存是吃饭,大众认为因爱书而走火入魔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而懒得答理随他胡言乱语。 去年夏天某日,在北京城南报国寺有个约会,事先我约了止庵先生一道去,正好他没来过这古寺就答应来。报国寺里有个文化收藏品市场(以卖买古旧书为大宗),十年历史了,名气仅低于享誉全国的潘家园旧货市场。这天的约会,原本就六七个书圈里的熟朋友外加山东某报文化版的编辑,到了中午聚饭的时候,局面失控,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就是他的朋友就是大家的不分彼此,一个中等包间一张圆桌居然挤下了近二十口男男女女,央视某文化频道的两位不知什么时候也上座了。这些人我当然都了解,在藏书圈里玩了这么多年,浮出水面的都知道我,而止庵先生瞧着这帮人眼生,我跟他开玩笑,这不是你熟悉的读书圈,将就点吧,其实我们有共同话题——同为天涯爱书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只不过今天这伙子人侧重于收集古旧书,你呢,重于读而对版本不太讲究。散席之后,我问止庵有何评论,他回了八个字“高者近儒,低者近丐”,我说你骂人不带脏字,把我的朋友全否了,哪来的高者?后一句才是你的真实印象。虽然我一直警觉读书界对藏书圈(界比圈高)的偏见,不成想就是这码事——藏书圈的印象分历来不高,在旁人眼中,这是一帮不可理喻的家伙,神神叨叨,不着四六,总以为天底下唯有藏书是最要紧的事情,谁要是说他一句他的书不好,如数家珍的脸即刻就是晚娘之脸了。所以,我有责任把嗜书者分为两类,一类“嗜读书”,一类“嗜藏书”,井水不犯河水,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只有极个别天才,有能力平衡嗜读与嗜藏的辩证与统一,平庸之辈顾好一头即手忙脚乱。《嗜书瘾君子》这本书,我只看书名就猜到是谈“嗜藏书”者的,至少多一半的笔墨落在“藏”上而非劝君多读书,及至把全书阅过,先前的判断基本靠谱,虽然是外国人写作的,许多情况亦很符合我们的国情,移情换景,恰似量身定做,到底是天下爱书一家人,且看这一段人家说的话——“君乃寰宇大作家,只要书名页上所有作家,只消一眼便知其等级高低,版本种种了然于胸,其看重珍视精刊佳椠,犹胜对待维吉尔与赫拉斯,屡屡赞叹用纸如何精致,频频称颂藏家何等用心勤勉,每见秀雅铅字,便情不自禁满心开怀,仿佛如此这般,即已完成扎实学问,增进大量识见”(约瑟夫·阿迪生《汤姆·弗利欧行谊》)。藏家为读家诟病由来已久,其最大一宗罪即“只藏不读,只藏不用”,还有一潜台词“只藏不读也罢了,最看不惯那厮拿着所谓珍本满世界招摇”。而我们这里的一流藏书家说得更极端,说这话的是周越然(1885~1962)——“对于这种读书不考究版本的人,我可设一比喻。翻刻本或影印本,好比寡妇。至于随便石印本或排印的本子,简直是下贱的‘野鸡’。青年人娶妻,总希望一个好人家的女儿,不愿意与寡妇结识,或与野鸡谈恋爱的,所以真能读书者,必求精善的本子。”(“版本”原载1934年《太白》创刊号)如此伤众的言论搁今天哪还不招来如雨般砖头,当年却波澜不惊,只有两篇响应,宋云彬一篇(“也谈版本”刊《太白》),名气现在比周越然高得多的藏书家阿英一篇(“版本小言”收《夜航集》),这两篇均细雨和风,一丁点儿急赤白脸也没有,我分析,这与教养关系不大,以上世纪三十年代论战风气,什么难听的话说不出口,何以偏偏对周越然宽容?鄙意当时的嗜书如命者只是很小很小的一小撮,更多的群体首要考虑的是生存是吃饭,大众认为因爱书而走火入魔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而懒得答理随他胡言乱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