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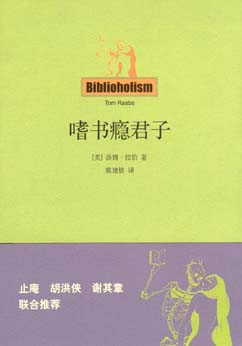 春节长假里读董桥先生一篇旧作《初版水仙花》,说他从前在英伦淘书的故事,其中有“中外集藏书籍文玩的人情怀一样:搜猎的历程是最大的乐趣,拥有了反而往往淡然了。坊间我们买得起的初版好书不多,搜猎的时日长,向隅的遭遇多,共过患难的感觉浓,交情自然深了”。说的是依各人眼光与品位的淘书经历,多数爱书人都曾感同身受。那时候董桥正与几位喜欢书籍的知己意趣相投,大家每周聚在一起喝咖啡交流谈论各自淘书所得,慢慢消受淘书带来的美好时光。董桥在这里对喜爱书籍的人没有严格划分,一声“曾为梅花醉不归”的叹息,恋恋红尘中共患难的感觉,决定彼此藉以成为朋友。 春节长假里读董桥先生一篇旧作《初版水仙花》,说他从前在英伦淘书的故事,其中有“中外集藏书籍文玩的人情怀一样:搜猎的历程是最大的乐趣,拥有了反而往往淡然了。坊间我们买得起的初版好书不多,搜猎的时日长,向隅的遭遇多,共过患难的感觉浓,交情自然深了”。说的是依各人眼光与品位的淘书经历,多数爱书人都曾感同身受。那时候董桥正与几位喜欢书籍的知己意趣相投,大家每周聚在一起喝咖啡交流谈论各自淘书所得,慢慢消受淘书带来的美好时光。董桥在这里对喜爱书籍的人没有严格划分,一声“曾为梅花醉不归”的叹息,恋恋红尘中共患难的感觉,决定彼此藉以成为朋友。
不过爱书人与书痴到底有所区别,美国人汤姆·拉伯据自己的淘书经验和爱书心得,说:“有两个名词曾被用以区分两种迷恋书的行为:bibliophilia(书之爱)与bibliomania(书之痴)。两者之间以基本心态之不同粗略划分。书痴竭力于搜书、藏书,而爱书人(尽管也并不排斥收藏书籍)则用心在求取书中的知识与智能。”大概这就是我们所要甄别的爱书人与书痴的定义。因此这本书的原名《biblioholism》被译为《嗜书瘾君子》,就有“书痴”与“爱书人”兼收并蓄的意思,堪称妙笔。
若单看《嗜书瘾君子》书名,便知又有某位痴人被书籍“撞了一下腰”,雅兴之事只因“我为书狂”,倒也尽兴。虽然坊间关于书或谈书淘书爱书一类的书籍已经出版很多种,但似乎仍不能满足对书籍深怀痴情的读者。自从八十年前那位美国老叟爱德华·纽顿以《藏书之爱》开俏皮之风,其后那些谈书访书猎书的文字多少都染上这种美国习气。《嗜书瘾君子》作者显然受其影响,走的也是幽默俏皮的文风,自说自话的美国式噱头为逗引起读者掩襟一笑,也为释放自己隐藏于心的淘书之乐。汤姆·拉伯《嗜书瘾君子》虽无仪态万方之丽,却有口吐珠玑之质,通篇都是嗜书的闲情适趣,妙语横生。倘使从出版时间推算,当是我读到写作年代最近的一本书痴呓语。它的版权页上注明初版在2001年,因此它所谈叙的趣事和语言也就更为贴近我们现在的生活。尽管书中很少谈及作者自己的淘书历程,但书里那些对书痴无可救药的自白,足令这世间广大书虫们欣喜。过去绅士们冲冠一怒为好书,不免要受到腹诽而耿耿于怀,但放在今天,则被视为佳话四处传扬。这表明人们对待时世有了更多宽容。多数情况下,《嗜书瘾君子》靠自我嘲解来叙述书痴冷暖自知的淘书人生,借此引发读者共鸣。尤其一句“嗜书瘾君子的存在由两部分组成:买书、看书。此乃生命之所以值得延续下去的重要理由”,大抵可视为《嗜书瘾君子》为书痴立传的名言。
《嗜书瘾君子》全书分有十四章谈论关于书籍的话题,另加一章“后话”叙述逛书店的奥妙,读此可知作者嗜书的程度。与其他书痴淘书所写的书籍不同,汤姆·拉伯将书痴的各类症候,用一个章节“病症剖析”来讲叙,分“生理症状”、“居住环境”、“生活品质”、“末期病状”和“嗜书瘾小常识:性格缺陷抑或生理病症?”将这些与书相关的毛病一网打尽,让患此症状的书痴们对号入座。“我们与书本的情爱之路,一路走来,理性与痴狂之间往往只隔一线”,头头是道的说教只为自我检讨之后,获得情深似海的读者会心微笑。
另一章“旁症博瘾”谈论“读瘾”、“嗜书网痴”、“学究”、“葬书狂”、“书刽子手”这些与书有关的另类瘾症,说来说去,则“一言以蔽之:一样米可养百种嗜书瘾君子——其中若干患者的病情甚至一个比一个严重”,颇使人颔首。
机智风趣虽是《嗜书瘾君子》一大特色,但书中语言过于调侃,免不了闲杂琐语,让人觉得美国式夸夸其谈未免华而不实,譬如:“想要像莎士比亚那样子出口成章吗?把《奥塞罗》剁一剁、加进《哈姆雷特》熬成一大盅端上桌,吃它几口,保证你从此饱腹诗书、满满一肚子好文章。”尽管极尽风趣,却也不免要损伤叙述内容的严谨与完整。从这个角度来讲,原作与译笔之间的“信、达、雅”更耐人玩味。
从全书看,似乎翻译者陈建铭的个人语言更有趣味。借着他翻译那部《藏书之爱》作凭据,文字的机智灵活在他手里已臻老谋深算地步,仿佛这书成了陈建铭个人的风味展示,大有超过原作者的表现。像“咱们还是希望能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客观地审视这种瘾头”一类,便很有我们时代的语言风格。另一方面,作者汤姆·拉伯对尤金·菲尔德《书痴留情录》惜惜相怜,常引述到自己笔底作陪嫁新娘。这里补充一句:尤金那本《书痴留情录》前几年有大陆译本由中华书局出版,书名译为《书痴的爱情事件》,台湾与大陆两个书名的译法不同,意思相去甚远。话说回来,将《嗜书瘾君子》与《书痴的爱情事件》两书对照来读,近似的幽默与俏皮文字,正可体会另一种书痴情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