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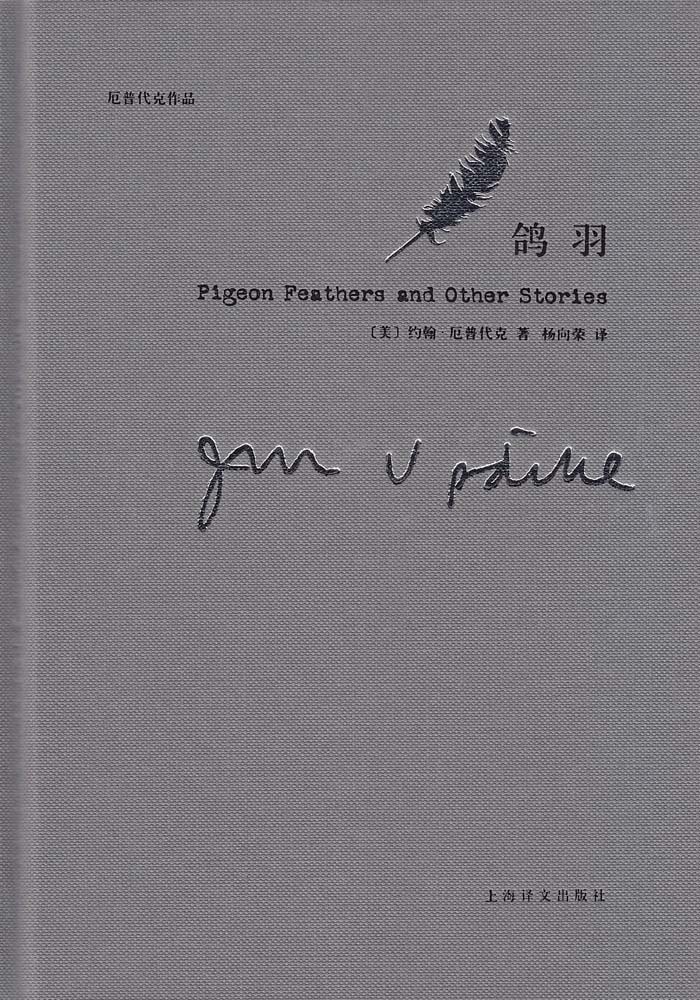 跟很多人一样,我是从厄普代克的长篇小说读起的,《马人》和“兔子四部曲”我一读再读。但对于他自认成就更高的短篇小说,却因为之前国内译介不多而没什么概念。直到读了2003年的《爱的插曲》(上海译文)和2012年出版的《父亲的眼泪》(人民文学),才算有了初步的印象。尤其是后者,这部他在生命终点前完成的小说集里的多数作品质量之高、功力之深厚着实令人惊叹。这也让我对于他的其他短篇集有了更多期待。 跟很多人一样,我是从厄普代克的长篇小说读起的,《马人》和“兔子四部曲”我一读再读。但对于他自认成就更高的短篇小说,却因为之前国内译介不多而没什么概念。直到读了2003年的《爱的插曲》(上海译文)和2012年出版的《父亲的眼泪》(人民文学),才算有了初步的印象。尤其是后者,这部他在生命终点前完成的小说集里的多数作品质量之高、功力之深厚着实令人惊叹。这也让我对于他的其他短篇集有了更多期待。
在《鸽羽》之前,厄普代克已经出了两本长篇小说、一本短篇小说集和一本诗集。尤其是那本《兔子,跑吧》,证明他作为一个作家已然成熟。
作为进入成熟期后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鸽羽》里展现出的是厄普代克后来很多作品里反复出现的题材:宾夕法尼亚州日渐衰落的小镇上的普通家庭生活,懵懂少年与家庭的矛盾情结,郊区中产阶层男女的感情纠葛、尤其是情感能量的衰竭与无望的拯救,还有对死亡的思考。
▼ 并非19个短篇小说合集 ▼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小说集并非只是十九个短篇小说的合集,而是有结构的一个整体——它是一部整体意义上的作品。
一方面是内容上的,其中比较重要的小说比如《鸽羽》、《波士顿的幸福男人,外婆的顶针以及范宁岛》和《硬地,教学礼拜,一只垂死的猫,一辆换来的车》写的是同一家庭不同时期的事;而《沃尔特-布雷吉斯》、《魔法师应该打妈咪吗?》和《林中乌鸦》写的是另一家人的事。即使是《高飞》和《庇护感》这两个写不同少年人物的,也会让人觉得他们好像生活在同一个地方。
另一方面,位于小说集中部的那个超短篇《大天使》看上去其实更像是来自于《圣经·诗篇》里的颂诗,朴素、绚丽而又神秘,也像是在整部作品最高处或最深处燃烧跃动的一簇灵魂之火,散射着奇异莫名的光辉和足以让其他作品缓慢围绕着旋转运动的不可探知的能量。而在它后面不远处的那篇《救生员》则更像是一篇关于情欲、美与愉悦的“布道词”。
因此总的来看,当你把这些小说从头到尾读一遍之后,会觉得单独看任何一篇都会有种悬置感和待续感,每一篇终了之际似乎都在呼唤着别外某一篇……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关联,甚至里面的那些人物也都像是彼此认识的——当然,他们都活在这本书的世界里。
把短篇小说集当成一部整体性的作品来处理,我认为厄普代克很有可能是受了他所推崇的塞林格的那本《九故事》的启发,只是他采取的结构方式别具一格而已:《鸽羽》就像一部由不同的乐器在不同的声部围绕着主副旋律时而此起彼伏时而交相呼应地演绎出的交响诗。正像杰恩·帕里尼(Jay Parini)认为的那样:
“没有人可以像厄普代克那样,抓住宾夕法尼亚那个地区的空气的特殊气息与味道……《鸽羽》或许仍是他这方面最好的故事集。”
《鸽羽》中分量最重的显然是那篇同名小说。这篇杰作之所以重要,一方面是因为它涉及一个少年成长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信仰的动摇、死亡的恐惧、家庭的矛盾,甚至是城市与乡村的根本价值冲突,以及与这些相关的种种内裂。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它充分反映出厄普代克的生命美学观:在天地之间、在永恒与短促之间、在生与死之间,如果还有什么有可能让微不足道的人获得某种意义上的解脱的话,那就是创造之美。
厄普代克的厉害之处在于,他让那个叫大卫的少年在焦虑得身心俱疲、即将被各种矛盾和对死亡的恐惧拖入绝望的深渊之际,忽然赋予了他以暴力的方式解决问题的机会——他极不情愿地拿着作为十五岁生日礼物的来复枪来到自家的谷仓,根据母亲的要求,对栖居在那里的鸽群展开了杀戮。在此之前没有人会想到这个杀戮事件会出现并将占全篇的五分之一,同样更不可能想到这个残忍血腥的事件竟会让大卫意外地发现了造物之美:
“他完全迷失在鸽羽优美的几何潮水中,这时鸽羽变宽了变硬了,好像要斜起某个角度飞翔,然后又变软了收缩了,为无声的肉身罩住体温。整个羽毛表面显示出的功能技艺,既像经过无穷无尽的调整校准,又像毫不费力取得的,鸽羽颜色的设计浑然天成,没有两根是重复的,仿佛在某种高度克制的狂喜中设计出来,这种喜悦就高悬在他头顶他身后的天空中。”
甚至还让他感受到有可能让他解脱的道理:
“上帝对这些毫无价值的鸟儿都慷慨施以如此鬼斧神工,他当然不会因为拒绝让大卫获得永生而毁了他全部的创造。”
整篇小说就这样,从纠缠不清的矛盾状态一步步累积到了后面突然爆炸般的状态,然后是通往解脱的释然与宁静,厄普代克对于压抑焦虑气氛的营造,对于整篇节奏的控制,以及在最终推向异常强烈的高潮时对于暴力美学的极为精到的把握,真可以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