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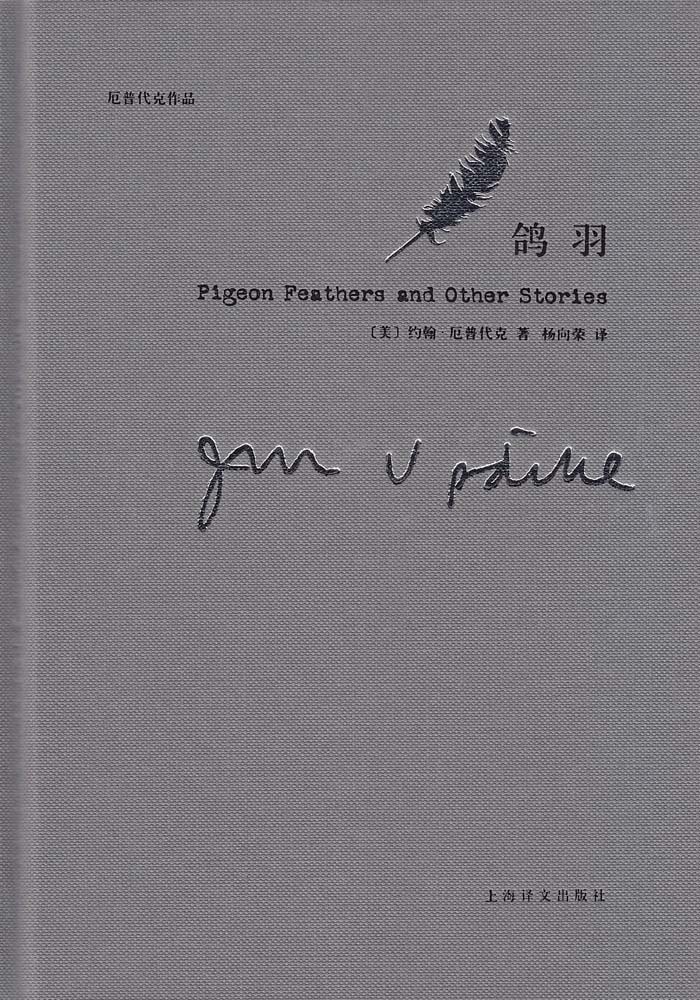 罗伯特的喉咙像被一片网状的东西堵住了。他打了个喷嚏。“可怜的罗比尔,”母亲说,“我敢说上次在家后没再犯过干草热吧。” 罗伯特的喉咙像被一片网状的东西堵住了。他打了个喷嚏。“可怜的罗比尔,”母亲说,“我敢说上次在家后没再犯过干草热吧。”
“我都不知道他得过干草热呢。”琼恩说:
“噢,挺凶的呢,”母亲说。“他小时候犯这种病可让我操碎心了。加上鼻窦炎,其实他真不该吸烟。”
车里的人全都忽然向一边摆过去,原来人行道旁一辆车出其不意窜到他们行驶的路上,父亲没有踩刹车,来了个急转弯绕过去。那是一辆长长的绿色车子,新得锃亮锃亮。司机座侧的窗口里那张面孔,在罗伯特他们的车子急转弯的刹那像忽然打住运动的皮球,满脸惊骇,涨得红彤彤的。罗伯特模模糊糊地看到发生的事。他的眼睛里噙着泪水。车继续往前开去,走了半英里远,他才醒悟到越来越大的喇叭声的目标是对着他们来的。那辆绿车正加快速追赶他们,跟在他们车后,离保险杆只有几码远,司机差不多把身子靠在喇叭上。罗伯特转过身透过后窗看见,在翘起的眉毛般的金属罩下三盏一组的两个头灯之间,散热箱的格栅上镶着OLDSMOBILE一串长形字母。那辆车猛然冲进相邻的车道,然后放缓速度跟他们的车齐速并行,车的流线型完全不像回事了,往后仰的挡风玻璃就像快要掉了的帽子。那个红脸小个子司机冲着靠近他们这边的窗子大叫大嚷。他的中年妻子好像已经是这类表演的老搭挡,娴熟地把脑袋缩到后面,好让他的话飘过来,然而在急风和吱吱转的轮胎声中,听不清他在说什么。
父亲侧耳倾听,难受极了,便转过来问母亲:“他在说什么,朱丽亚?我听不清他说什么。”虽然他在这地方已经住了三十年,还不时要拿妻子当翻译。
“他说他是个脾气暴躁的人。”母亲回答说。
罗伯特正喘着气酝酿着要打喷嚏,脑子给弄得雾蒙蒙的,跺着脚想要车子开得更快些,好把骚扰者甩掉。可父亲却放慢速度,把车刹住了。
那辆奥兹吃了一惊,向前超了他们好一段也在路边停住。这时他们还在市镇外面。炎热的公路两侧起伏着美丽而整齐的田地,在飘扬的花粉中显得如薄雾般朦朦胧胧。前面那辆车像啐唾沫一样,吐出了里面的司机。一个矮胖的男子迈着胖子特有的小跑步一颠一颠地顺着煤渣铺的路边向他们跑过来。他身穿一件夏威夷花衬衫,满嘴不停地喷着话。普利茅斯牌旧车的马达连续转了四个小时,热得没法空转,震颤了几下后就熄火了。那人的脑袋出现在车窗侧面,方方正正的头盖骨,小小的白耳朵上方隆起好几道软骨,因为胡言乱语,肤色涨得通红,发皱,给人以一种柔嫩闪亮的印象,像是香肠的外皮。没等这人缓过气来说话,罗伯特就认出他属于优质品质,外界由于无知的偏爱而称之为宾夕法尼亚荷兰种。
接着,在第一波飞瀑般的尖声怒骂中,他的口音中浓烈的ch音和错位的w音显得格外醒目,就像顺着瀑布冲下来的破木条箱上印的一个个字母。疯狂的声音低下来,变慢了,这时一串串下流话才清楚了。连贯的句子也能明白了。“你某(没)权那样挡我的车!你某(没)权在镇上那样开车,”罗伯特的父亲不做任何回答。这副不屑的态度像抽陀螺般把那红脸矮个子的怒气又抽得发作起来。他皮肤亮闪闪的,好像马上就要迸裂了。他把脸戳进他们的车窗里。他紧闭双眼,眼皮肿胀,鼻孔两侧因为太用力而胀得发白。他的声音忽然哑了,好像嗓子被自己的声音吓坏了。他转过身离开一步,那耀眼的动作好像在跟一种步步紧逼、丝毫不让的巨大力量对抗了一番后才完成的。
罗伯特的父亲慢条斯理地从后面叫住他说,“我使劲想理解你的话,先生,可就是不明白你的意思。搞不清楚你想说什么。”
这下又把陀螺抽转了,而且转得更疯狂,不过持续的时间比较短。母亲挥手赶走面前的几缕烟,乘机放松了下僵硬了好久的身子。婴儿叽叽咕咕闹起来,琼恩向前座位边沿挪了挪,打算去面对这场骚扰的源头。也许两个女人的动作让那个荷兰人动心,感到有点愧疚,就像发表补充性的法律论据似的又喷射了一通公厕墙上的那些话语。那双白亮的手犹如通了电般在他的衬衣的花朵中挥舞了几下,而且还真像苦行僧那样,旋风般地完全转过身来。罗伯特的父亲眼神凄凉地凝视着这团旋风的中心,脸上的皮肤变得越来越黄,仿佛又回到了过去反复拔牙的情景。从侧面看,他双唇固执地紧闭着,遮住粗苯的牙齿,眼睛像颗圆溜溜的钻石,专心注视着。这副专注的神态拖住了荷兰人愤慨的劲头。在正午奇异的声学效果中,那伤心不已、满嘴下流话的声音,像是从大家头顶上那烤盘似的蓝天挡了回来,摩擦了一下,打住了。
好像那点火星儿刚碰到肚子上,科琳又尖叫着哭起来。琼恩蹲下身冲前窗喊道:“你把孩子闹醒了!”
罗伯特两腿酸疼,一半是为了伸伸腿,一半是为了表示气愤,打开车门下来。他感觉自己裹着黑色英国正装的细长身材像件优雅而出其不意的武器般舒展开来。对手犹豫地皱起冒着汗珠的前额。“你干吗在我们面前耍这套把戏?”罗伯特用懒洋洋的家乡口音问他。由于干草热堵住鼻子,加上刺眼的阳光减弱了声音,他的话音听起来不太像是自己发出的,倒像老熟人在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