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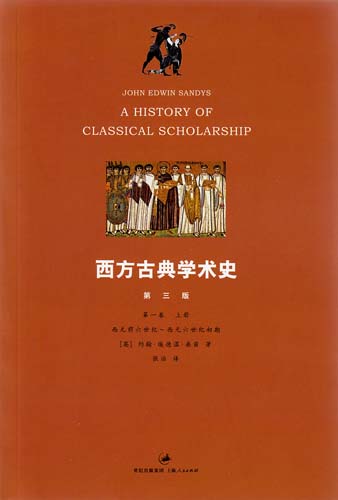 2010年年底,英国古典学者约翰·埃德温·桑兹的巨制《西方古典学术史》第一卷由张治先生翻译出版,大受好评。不轻易许可的高峰枫先生说,此书译事之艰巨,堪称“赫拉克勒斯的工作”,译者犹如“译界大力神”。最近,张治先生终于出版了首部个人文集《蜗耕集》,收录了关乎古典学、文学、中西交通史等领域的书评、翻译批评、随笔、演讲稿凡22篇,俱覃思精研,文采斐然,还有许多平常学术文章不能设想的谐趣。 2010年年底,英国古典学者约翰·埃德温·桑兹的巨制《西方古典学术史》第一卷由张治先生翻译出版,大受好评。不轻易许可的高峰枫先生说,此书译事之艰巨,堪称“赫拉克勒斯的工作”,译者犹如“译界大力神”。最近,张治先生终于出版了首部个人文集《蜗耕集》,收录了关乎古典学、文学、中西交通史等领域的书评、翻译批评、随笔、演讲稿凡22篇,俱覃思精研,文采斐然,还有许多平常学术文章不能设想的谐趣。
张治先生精通的领域,我是全然的门外汉,唯有仰慕。在此,只能抄一些张先生的高论,发表一些粗浅的个人感想以及“无力的赞美”了。更深入的品评、研究,亟待专业人士完成。
在《“这人不是死了,就是教书去了”》、《钱锺书读“娄卜”(二)——奥略·葛琉斯〈阿提卡之夜〉》二文中,张治先生均提到西方古典世界里的一类“庸才”,“痴迷于抄录生僻词汇来冒充学问的‘语法家’(这也可指教书先生)”(第91页)。在前一篇文章中,张先生提到古典时期叙利亚文人琉善(Lucian,又译卢奇安、路吉阿诺斯)生造了一个叫Lexiphanes的词儿,意为“炫耀生僻词汇的人”(第4页),用来讽刺这类“庸才”。初看到这个词,我立马就将之与张先生联系在了一起,盖因Lexiphanes正是张先生的网名之一,加上这词还可以指称张先生现在的职业之故。琉善造词,是为讽刺,张先生用为网名,或有自警警人之意?然而,在我看来,在刻下浮躁的环境中,悉心掌握大量“生僻词汇”的人是有炫耀的资本的。他们的炫耀,可用来敲击那些对字词无甚把握偏喜侈谈之人的脑门儿。翻开《蜗耕集》,我们可以看到中文之外,张先生“炫耀”了希腊文、拉丁文、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的“生僻词汇”(当然,这不是说张先生精通于上述所有语言),用之于古典文学、近人译作得失、中西吃蝗虫的“简史”、钱锺书读《堂吉诃德》的心得等大大小小问题的探讨。在这个框架内,他叹赏的对象如桑兹、钱锺书、李奭学以及译书时的鲁迅、周作人,也是“炫耀生僻词汇”这一面的形象较为突出。
“炫耀”的形式之一,便是罗列。《蜗耕集》中,《“列举”法的修辞学技艺与〈巨人传〉》是我读来特别有兴会的一篇文章。通过讨论《巨人传》的两个中译本(鲍文蔚译本与成钰亭译本),张先生指出,拉伯雷原著中稠叠不冗滞且有谐趣的连类排比、百科全书风格,两部颇为用心的中译本均无很好的体现,殊为可惜。“‘俳谐’、‘俳优’之‘俳’,与‘俳骊’、‘俳偶’之‘俳’,本是同源。滑稽突梯的效果,离不开形式上的奇思妙想,也离不开语言上的变化丰富,以为人民群众欣赏的笑骂文学,便是‘痛快’和‘粗犷’,这太片面了。”(第31页)在《我们今天如何读但丁〈神曲〉》一文中,也触及到了这个话题。
我们知道,钱锺书先生特爱连类排比,爱好者以为胜义缤纷,批评者以为是满地都是串不起的散钱。张治先生比对了钱先生的手稿《容安馆札记》与《管锥编》、《谈艺录》二书中述及罗马帝国时代希腊犬儒学派哲学家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Laertius)的地方,发现《容安馆札记》中不少资料并未见于《管锥编》与《谈艺录》。张先生的结论之一是,出于修辞的目的,钱先生对“堆叠”是有慎重考虑的,“有人谓钱博引而不知节制,又言不能如百科全书一样征引而至无遗珠之憾,这些看法都是想当然的议论”(第85页)。这让我想起法国诗人、批评家瓦莱里。他谈福楼拜时,拿歌德的《浮士德》与福氏的《圣安东尼的诱惑》对比,并引歌德对秘书爱克曼讲的话:“数不清的神话形象争先恐后要进去(《浮士德》),但我小心在意。我只采纳那些将我所寻找的图像送到眼前的形象。”(《文艺杂谈》第188页)瓦莱里说,歌德拥有福楼拜没有的“智慧”,后者始终被百科全书知识这个“魔鬼”所纠缠。可与此相发明的是,张先生说,但丁的一个创举在于借尤利西斯之口说:不要回家,要浪游世界探索知识。在《神曲·炼狱篇》十九歌中,漫游者但丁被塞壬的歌声所迷,这歌声“不是女色肉欲的诱惑,而是对于一切未知世界的知识,这才是最大的诱惑”(第191页)。不过,但丁后来还是摆脱了这种诱惑,也是要回家去的。这是否说明,但丁其实是站在瓦莱里这个队列的?现时国内也有作家喜谈百科全书式小说,不过恐怕只是侈谈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