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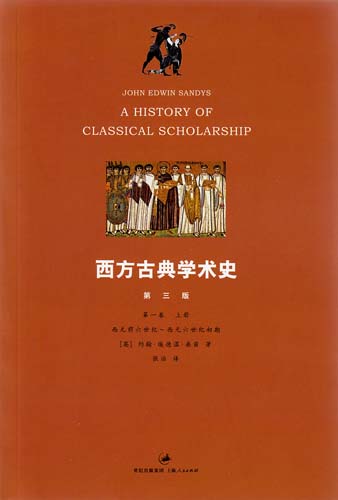 英国古典学家桑兹(John Edwin Sandys, 1844-1922)于一百年前撰写的三卷本《西方古典学术史》,由张治翻译,中译本第一卷已于2010年10月出版。报章上陆续刊登了一些书评、书讯,但大都简略,对中译本的特色也语焉不详。笔者不揣谫陋,想就桑兹这部大书(以下简称《学术史》)以及张治的译笔稍作具体的评述,希望能引起更多读者的关注。 英国古典学家桑兹(John Edwin Sandys, 1844-1922)于一百年前撰写的三卷本《西方古典学术史》,由张治翻译,中译本第一卷已于2010年10月出版。报章上陆续刊登了一些书评、书讯,但大都简略,对中译本的特色也语焉不详。笔者不揣谫陋,想就桑兹这部大书(以下简称《学术史》)以及张治的译笔稍作具体的评述,希望能引起更多读者的关注。
桑兹的贡献
桑兹的生平著述,译者张治在后记中已有介绍,兹不赘述。偶然发现的其他材料,补记于此。最近,蒙友人周运相告,英国古典学家格罗佛(T. R. Glover)在《剑桥忆往》(Cambridge Retrospect,1943年)一书中,用了相当篇幅回忆当年的老师桑兹。翻开这本薄薄的小书,发现桑兹当年由首相阿斯奎斯(Herbert Henry Asquith, 1852-1928)提名,被册封为爵士,正是凭借这部巨著(46页)。桑兹曾校勘、笺注古籍多部,但最为人推重的还是这套《学术史》。他在1922年去世之后,友人在剑桥一教堂中为他立铜匾,用几行拉丁文概括其一生成就。在涉及学术贡献时,只有“撰古学史”一语(studiorum antiquorum historiam conscripsit, 51页)。从铭文可见,这部书确已成了他身后的一块丰碑。
在西方学界,这部《学术史》至今仍被引述,网上仍可买到最新的重印本,在西人著述中仍能发现剿袭桑兹但又不注明出处者,可见我们的约翰爵士并没有沉入历史的“忘川”,仍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利用价值。提到桑兹的书,自然要提到一部晚出的同名著作,这就是鲁道夫·普费佛尔(Rudolf Pfeiffer, 1889-1979)的《古典学术史》。普氏是德国学者,上世纪三十年代因躲避纳粹的迫害,客居英伦,在牛津执教十余年,二战结束后方返国。他撰写的这部《古典学术史》,上卷从古代初期一直写到希腊化时代结束(公元前七世纪到前一世纪),于1968年在牛津出版。喜新厌旧是人之常情,学术亦然。常看到人们称许普氏的著作后出转精,并且诟病桑兹的芜漫庞杂。我们不妨先来看看普氏本人对桑兹的评论,于两人的异同或可得见一些端倪。
普氏在前言中,对曾经勾勒古代学术风貌的前代学人都有所论列。谈到桑兹这部巨制时,花费的笔墨最多,共写了十四行。普氏先抱怨前人的学术史篇幅均短小,分量不够,然后说:
内容无所不包的书唯有一部,这便是J. E. 桑兹的《古典学术史》。该书分为三卷,共计1,629页。等我们读了他的小传,了解了成书过程,我们对他便不免又是钦佩,又是嫉妒。他于1900年1月1日动笔,第一卷在1903年就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1906年第二版,1921年第三版),其余两卷则出版于1908年。这个三卷本还有1958年波士顿的重印本。此书虽然在很多方面有些过时,但作为一部经典著作,永远是不可或缺的参考书。后人再写学术史,必要感激这部材料丰赡、取材广泛的著作。不过,就整体而言,桑兹的著作实乃一古典学家的名录(catalogue),依年代、国家和著作划分,难称一部真正的学术史。书中缺乏一以贯之的主导思想,也缺乏贯通的结构。对于材料当中,何者属于朝生夕灭,何者有永久价值,则缺乏审慎的区分。(前言,第viii页)
普氏先礼后兵,对先贤脱帽致敬,然后就是不客气的批评。他的意见若概括来说,就是:桑兹的书,材料太多,识见太少;只可作案头翻检的工具书,但难称有远见卓识的学术史。
桑兹一书材料丰赡,是有目共睹的。一部一千六百多页的书,从对荷马史诗最早的校勘和赏鉴,一直写到十九世纪德国古典学的勃兴,堪比一座跨越两千五百年的长城。这座长城不是凭靠“思想”和“观点”硬撑起来的,而是由成千上万条具体的史料辛辛苦苦搭建的。读者展卷,只要读上十余页,便会惊骇于桑兹取材的广泛和穷尽(正是普氏所云“the range and thoroughness of its materials”)。这样的例子触手皆是,不能备举。我只举两个例子,以说明桑兹一书资料价值巨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