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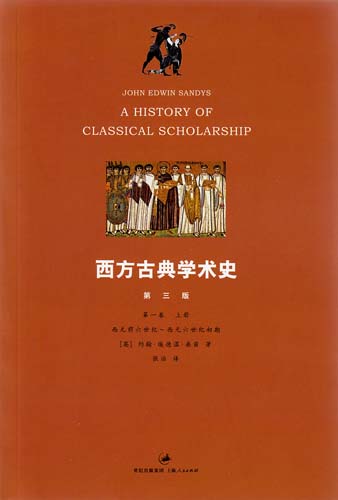 古典学研究的几种路径 古典学研究的几种路径
在古典学研究的著作里,十九世纪英国学者桑兹的三卷本煌煌大著《西方古典学术史》有着特别的气质,无论从精神还是体例上都显得如此与众不同。
研究西方古典学术的学者大概可以分为这么几类。第一类是那些世俗的,却又野心勃勃的古典研究者。他们当中的翘楚,上有公元前1世纪,研究古代神人制度的罗马学者瓦罗,中间有对罗马史念念不忘的马基雅维利,近有对古希腊哲学传统熟稔之至的尼采、海德格尔等人。一般而言,这些野心勃勃的研究者都会有一个核心焦虑,或者要重振邦国,或者要续写学脉。他们从古典学问的兵器库里寻找趁手的兵器,希望能在身边的世界一展身手。
另一类是那些受圣职召唤的,带有强烈献身色彩的研究者。这一类研究者的思想源头来自于《旧约》中的犹太苦修主义和《新约》中耶稣和使徒的苦修思想,还有一部分来自于比基督教稍早的诺斯替教,以及波斯的摩尼教等。或者更公允地说,几乎各民族的早期宗教都会有灵知主义和苦修的影子。苦修的途径之一就是潜心研读经典文本。他们中的极致,就是公元4世纪左右,在埃及兴起的沙漠隐修教父。在米兰敕令之后,这些人中的一部分转到了修道院,进而孕育了近代意义上的大学。
还有一类是古典学问的鉴赏者。他们没有什么世俗的野心和抱负,也说不上有使命征召的成分,更多的是出于个人的审美意愿,从鉴赏者的角度阅读古典学问。这类人基本上是文艺复兴之后的产物,比如歌德、施莱格尔等人。他们往往会在古典作品上投射强烈的个人色彩,赋予古典作品以当代内容;又或者在古典作品的慰藉中抵抗虚无的入侵和时代的无序,比如写作《希腊人和希腊文明》的布克哈特等。
如果说还有一类古典学研究者的话,那就是现代学术体系产生之后,以研究古典学为职业的大学教授。刻薄地说,古典学对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而言,只是一门手艺,和修理自行车没有本质的不同。
按照这个分类,桑兹很难算作他们中的任何一类,也不是史学界哪门哪派的大佬。关于他的生平,我们所知不多,美国学者汤普森在他的《历史著作史》里提到过桑兹,德国古典学者维拉莫威兹也不乏敬意地介绍他。桑兹1844年出生于英国莱斯特一个传教士家庭,受教育和任教职都在剑桥大学,1903年他出版了为他赢得盛名的《西方古典学术史》第一卷,在后来的几年里他对第一卷进行了两次修改,并于1908年出版了第二和第三卷。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位古典作品的校勘学家,先后编译过品达、欧里庇得斯等人的作品。
桑兹的“学问正路”
按照我们这边的说法,桑兹算是一个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小学”家,以整理古籍为业,不事宏大的理论生产,也不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夹带“私货”。桑兹生活的年代,是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太平年代。虽然在他出生不久,欧洲大陆爆发了1848年革命,又有英国参加的克里米亚战争,但英国本土在辉格党人的领导下还是一番盛世景象。19世纪中叶的英国工业处于世界绝对领先地位,一战尚远,因此,在桑兹的思想内部,不太会有紧迫的时代焦虑,加上他带有宗教色彩的家庭背景,他对待古典学问的态度比较平正。
在我看来,这种平正的治学态度是理解桑兹及其著作的一个基本背景。与之相较,他同时代或较早的历史学家或多或少都有些焦虑。比如德国开山立派的大史家兰克,尽管强调客观平正的历史,但背后还是隐藏着一个躁动不安的日耳曼幽灵;又比如布克哈特,身处欧陆中心,难免对19世纪的革命风潮产生反应,尽管这种反应是以一种间接而消极的方式作出的。
当然,我们大可以强调桑兹的“小学”家身份,或者更直白地说,他是研究“史料”的,不是研究“历史”的。但这种研究取向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桑兹是一个很悠然的古典学问研究者。比如,就桑兹的研究主题,“西方古典学术史”而言,什么叫西方古典学术,本身就是有疑问的。主流观点认为古典学术就是希腊—罗马文明,德国学者维拉莫威兹明确地界定古典学术的本质,“(希腊—罗马)文明是一个统一体,尽管我们并不能确切地描述这种文明的起始与终结;该学科的任务就是利用科学的方法来复活那已逝的世界”。
这种观点并不是没有反对者。意大利当代古典学者莫米利亚诺就提出,希腊文明有着多元化的东方背景,希腊史学深受波斯史学影响,罗马史学继受希腊史学也并非天经地义,总之希腊—罗马文明并非浑然一体。莫米利亚诺的史学雄心更大。
与他们相比,桑兹既没有焦虑,也没什么野心,天然而不加反思地游荡在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以来的古典学传统,在他看来,那些争论都是浮云,我只要把这一领域内的文献整理好就行了。
桑兹的确也是这么做的,翻开《西方古典学术史》,那种涸泽而渔、一网打尽式的写法让人深为纠结。读桑兹的书,既没有汤普森那种文史兼备的通透,也没有莫米利亚诺式的犀利,同时也没有维拉莫威兹的简洁。对大部分读者而言,这样的著作只是聊备查阅的工具书。幸好,译者雅驯的文笔给我们带来了可遇不可求的阅读快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