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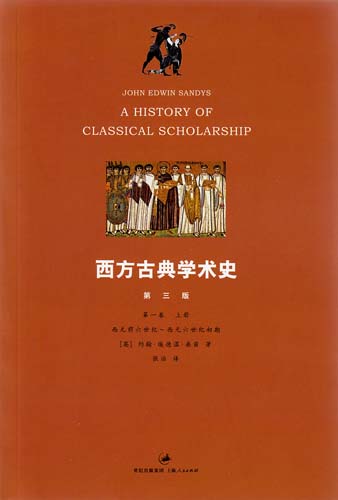 仅就西方古典学术史研究而言,国内的学者仍处于“转述、介绍”阶段,能介绍得明白就已经相当不错了,何谈深入研究?当务之急,是应该把西方主要的研究文献拿过来,明白人家到了什么程度,从而再进行研究与提高。 仅就西方古典学术史研究而言,国内的学者仍处于“转述、介绍”阶段,能介绍得明白就已经相当不错了,何谈深入研究?当务之急,是应该把西方主要的研究文献拿过来,明白人家到了什么程度,从而再进行研究与提高。
在出版人周运看来,学术史就是一张地图,不同作者、不同作品在里面分别占领着省会、地级市或县级市,于是后人才可以按图索骥,什么地方都可去得。可惜,国内学人在这张地图上下的功夫不够,无论是对西方学术史的研究,还是对中国学术史的研究,地图总是画得残残破破。
转述而已,何谈研究
周运本人酷爱西方古典学,经常会看这一类的外文书籍。偶然间,他发现国内一位十分有名的西方古典学学者的论文,几乎全部抄自一本外文书,当作访问学者的成果发表。“这也太明目张胆了,别说是自己的成果嘛,直接说翻译于某某书还更为确切。”
周运说,仅就西方古典学术史研究而言,国内的学者仍处于“转述、介绍”阶段,能介绍得明白就已经相当不错了,何谈深入研究?有些人在吹嘘,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西方古典学”,这就让人觉得搞笑,西方古典学就是西方古典学,何必借用各类名称?
周运曾与北京大学的一位老师探讨,假如国内派一批学者去国外研究西方古典学,会怎么样?这位老师回答:“十有八九都得读疯喽!”因为,在国外研究西方古典学,必须过语言关,得分别掌握古希腊语、拉丁语,拉丁语在不同阶段还有不同,这样才能去阅读浩如烟海的原始手稿。在国内,同时懂这两种语言的学者都不一定有,何谈学术研究?大多数人其实都是在英译本的基础之上,向国内作了些转述而已,少有能够与国际接轨的学者。
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应该把西方主要的研究文献拿过来,明白人家到了什么程度,从而再进行研究与提高。相比而言,日本这方面会好一些。前段时间,日本当代著名的美学家、哲学家今道友信的《中世哲学史》,在国际上获得了非常高的评价。
对自己的研究,也不如以前
周运认为,中国人对自己的学术史研究,以前有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再到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最近的有例如桑兵的《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等等。可是现在,研究状况也不如以前。
广州的胡文辉写了一本《现代学林点将录》,他虽然只是一名媒体人,不在学术界作研究,但功夫却做得扎实,虽然书中有些缺陷,但整体而言是非常不错的。看了这本书,我们会想“学术界的人都在做什么?”这的确是让人觉得有些丢脸的事。中国缺乏做基础性工作的学者,研究、出版都跟风严重,潜下心来做系统研究的人太少了。
学术史出版,需要及时更新
具体谈到近日世纪文景的《西方古典学术史》,周运说,桑兹的这本书,只能算是这个领域较为重要的著作,并不是代表最新水平。桑兹的《西方古典学术史》,实际上是集中了西方古典学家的传记,准确来说,应该叫“西方古典学家传”,而不是“史”。作为一部参考资料,桑兹的《西方古典学术史》的确非常重要,国内学者把它当成词典来用,比较合适。
周运认为,一部真正的学术史,不仅要有翔实的材料,还应该有对史实的判断。其实,桑兹的《西方古典学术史》已经被超越,目前在西方,最新的是费佛(Rudolf Pfeiffer)的《西方古典学术史》,不过因为版权原因,想看到这本书的中译本还有待时日。费佛颠覆了桑兹的许多说法,比如卡利马科斯主持古代著名的亚历山大城图书馆期间,编辑了120卷的独特的辞书《文化界名人及其作品概览》,这本书被称作西方第一部学术史。费佛的书中,给了卡利马科斯很多页的叙述和评价,而对桑兹只给了一页。
同样的例子还有,比如国内目前对西方文艺复兴的学术研究,还局限在布克哈特身上,他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直被认为是关于文艺复兴的最重要的著作。但实际上,目前在西方代表一个研究高峰的,是加林的《意大利哲学史》。布克哈特的研究侧重文学、音乐等文化史方面,加林的研究则是从哲学流派开始,而哲学正是文艺复兴最为关键的因素。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对历史学家的评价会发生变化,在不同时期,对某人的评价会不同。因此,学术史类图书的出版,也应该跟上最新的步伐,就像地图也需要更新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