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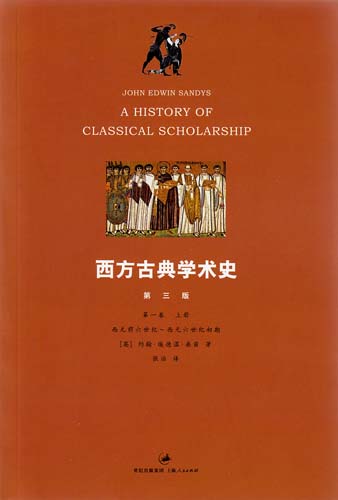 逝者如斯。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真正的史家于叙事中藏奥赜,于白描中求深远。史心如鉴。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作者与作品和读者休戚与共,他依读者品性绽放自己的世界,或凭高远视,如君临万众,鼓其奋勇;或俯视千载,如鸿鹄之鸣,声入寥廓。读者凭理解进入历史的时空,经验意义的真理和生活真理。他若与作者相通相契,在穿越历史的丛林时,自然可以听到逝者的歌唱:树林美丽、幽暗而深邃,我有诺言尚未实现,还需奔行百里方可沉睡。 逝者如斯。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真正的史家于叙事中藏奥赜,于白描中求深远。史心如鉴。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作者与作品和读者休戚与共,他依读者品性绽放自己的世界,或凭高远视,如君临万众,鼓其奋勇;或俯视千载,如鸿鹄之鸣,声入寥廓。读者凭理解进入历史的时空,经验意义的真理和生活真理。他若与作者相通相契,在穿越历史的丛林时,自然可以听到逝者的歌唱:树林美丽、幽暗而深邃,我有诺言尚未实现,还需奔行百里方可沉睡。
约翰·埃德温·桑兹(1844~1922)长期在剑桥从事古典学研究,自1903年至1908年剑桥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他的三卷本《西方古典学术史》,这部鸿篇巨制的问世已逾百年,此后的学者或删繁就简,或评文论史、各抒己见,然而就史料翔实这一点而言,桑兹之后,无出其右者。
西方古典学术史在严格意义上是指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学术历史,在宽泛意义上也包括其后各个时代的接受史。桑兹的这部著作在广义上立论,这样,他就不得不与大量的文本搏斗,追寻古典著作的历史命运,寻找它们的接受痕迹。桑兹的这部著作秉承如下宗旨:古典学术用希腊拉丁等语言作为手段,以理解逝去岁月托留于我辈的文学遗产;其为符咒,从时间坟墓唤集千秋万邦之伟人的思想意绪;其为路径,自此追踪人类社会、道德、知识与宗教的演进。全书共六篇,按历史时期划分为雅典时期、亚历山大里亚时期、罗马时期的拉丁学术、罗马时期的希腊学术、拜占庭时期、西方中古时期。每一篇篇首的年表是作者叙事的总纲。这部巨著涉及文学、史学、哲学等领域,囊括文献学、版本学、词源学、语法学诸端,可谓是“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
每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精神结构、感觉方式和体验方式。人类思想、感情、体验的历史“源头盲昧,活水奔流”。从何处开启古人精神和情感世界的大门?如何展现古人内心生活世界的结构?我们如何与古哲为友,与先贤同憩?这是桑兹的这部不朽之作要为我们解决的问题。历史学家通过运用自己“述而不作”的功夫,将文献资料编织成一幅“思想的织品”来展示历史上不同生活群体的精神风貌,真知灼见隐于织品精致的结构中。作品充实而有光辉,“光而不耀”者方为上品。桑兹的这部两次再版的《西方古典学术史》堪称此类佳作。
桑兹的《西方古典学术史》第一卷从公元前600年的《荷马史诗》一直写到1453年突厥人征服君士坦丁堡。雅典、亚历山大里亚、罗马、君士坦丁堡、意大利是2000年岁月之流冲积成的“文化之洲”。这些“地方”曾经是进行符号性交换和文化创造之所,正因如此,它们不再是地理学意义上的“区域”而成为“文化地层学”意义上的一个“空间”。那个空间里装着古人的激情与梦想、沉思与希望。我们如何进入这个“探梦空间”?如何与古人休戚与共?学习古典的目的不是躲进故纸堆里成一统,不管冬夏与春秋,而是要温故知新,丰富我们当下的生活。假如我们对古人不信不好,那么我们当下的创造必然会陷入冒昧危险之途。
为此,我们就必须深入到文化地层的深处,沿着它的纹理与脉络发现它的内核,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剥离时代性的重重“话语包裹”,洞见人类生活样态、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的过程。当我们从地层深处钻出,在时间结构里重新叠置这次“知识考古”之旅的收获,我们就创造了当下的新生活。要想使雅典、亚历山大里亚、罗马、君士坦丁堡与我们发生密切的关联,我们就不能单在“空间里游牧”,而且要在“时间里游牧”。读者作为“思想的牧民”如何才能使自己的游牧生活过得充满生趣呢?通过阅读桑兹《西方古典学术史》得到些启示。
藏诗心以入史境
诗的气息救活了19世纪的历史研究。曾经是苍白无趣的东西,诗让它变得生动形象;曾经是冷冰冰无生命的东西,诗让它恢复温暖和生机。桑兹的这部不朽之作就是在这种精神氛围中完成的。了解这一点是理解桑兹鸿篇巨制的基础。桑兹在第一编第一卷——雅典时期(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00年)中关注了以下六个主题:史诗、抒情诗、戏剧诗、修辞学的兴起和散文、语法学和词源学的发端。史诗、抒情诗、戏剧诗是雅典时期人类感情和思想的独特样式。诗是人类心灵的初级形式。没有诗,思想就不能产生;没有诗,就不可能有哲学,就不可能有人类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