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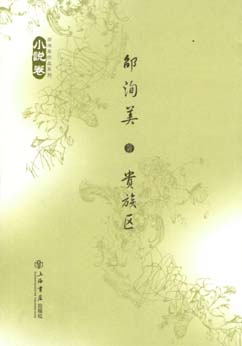 一个文人的大起大落乃至命运的不可预测性,留给后人的感触总有相近相似之处 一个文人的大起大落乃至命运的不可预测性,留给后人的感触总有相近相似之处
无缘见到邵洵美先生。潦倒落寞的他,在承受了牢狱折磨和“文革”震慑的一连串磨难后,一九六八年便告别了这个世界。十年后,当我一九七七年有幸参加高考走进复旦大学时,上海哪里还能见到他的身影?最初的文学教科书里,也难寻他的名字。读他的作品,是在后来;知道他的故事,主要借助于他的同时代人的回忆。不同的人,不同的讲述,一个人的命运,泼墨而成一片五色斑斓:美妙、飘逸、传奇、委屈、感伤、悲凉……
同时代人笔下的邵洵美
我所交往过的文化老人中,唐瑜、马国亮、黄苗子、丁聪等先生,都与邵洵美熟悉。早在上世纪的三十年代,他们与邵洵美相交往,一起活跃在上海文化圈。年龄上邵洵美比他们大不了多少,文坛辈分却算得上他们的前辈,编辑文艺刊物,则是既合作,又竞争。丁聪先生曾对我这样说过:“当时上海有两个画报系统,良友出版公司属于广东帮,有《良友画报》等好几个刊物。时代图书公司属于上海帮,有张光宇、鲁少飞、叶浅予,以漫画家为主,邵洵美做老板,刊物有《上海漫画》、《时代漫画》、林语堂的《论语》等。”
丁聪、黄苗子虽在“良友系”工作,却与“时代系”的关系也颇为密切。譬如黄苗子先生,谈到邵洵美,他总是怀着感激与敬重。一九二九年,他在香港还是中学生,向叶浅予主编的《上海漫画》投稿并获采用。这对他是一个极大的激励,两年之后,他与父母不辞而别,只身来到上海,随后成为文化圈的一员。在他的记忆中,邵洵美爽快而慷慨,既有才识,又有财力,引进世界上最新印刷机,用上好纸张,装点出上海期刊出版的一片美丽亮色。
丁聪不止一次在聚会中兴致勃勃地回忆一件往事。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邵洵美拥有中国最好的一套彩色印刷设备,时代变迁,他已不再可能拓展业务,遂决定出让设备。丁聪时任《人民画报》副总编辑,他专程从北京前往上海,与邵洵美洽谈转让事宜。丁聪印象中,走进新时代的邵洵美,早已没有了以往的潇洒和飘逸,曾被鲁迅讽刺和批评过的他,似乎预感到自己迟早将被新时代抛弃的结局,显得落寞,甚或有些焦虑。他已经不再可能从事出版,这套设备没有了用武之地。他与丁聪没有讨价还价,以不高的甚至相对低的价格,让丁聪把这套设备运回北京,交由《人民画报》使用。丁聪说,之后,他再也没有见到过邵洵美。
知道邵洵美后来的行状,是读了恩师贾植芳的回忆文章《我的难友邵洵美》。“他身材高大,一张白润的脸上,一只长长的大鼻子尤其引人注目。他穿了一件古铜色又宽又长的中式丝绸旧棉袄,敞着领口,须发蓬乱,颇有些落拓不羁而又泰然自若的神气。”这是贾先生一九五○年第一次见到邵洵美时留下的印象。这一年,也是邵洵美把最好的印刷设备忍痛割爱之际。落拓不羁,泰然自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与丁聪记忆有所差异的另一种状态。
状态虽有不同,一个文人的大起大落乃至命运的不可预测性,留给后人的感触总有相近相似之处。黄永玉先生虽没有见过邵洵美,却对其人生旅程的辉煌与悲怆有一种透彻的感悟,为此,几年前他还特地写过一首短诗:《像文化那样忧伤——献给邵洵美先生》:
下雨的石板路上
谁踩碎一只蝴蝶?
再也捡拾不起的斑斓……
生命的残渣紧咬我的心。
告诉我,
那狠心的脚走在哪里了?
……
不敢想
另一只在家等它的蝴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