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后,解释结果型过程追踪(explaining-outcome process-tracing)试图为某一特定历史个案中出现的谜之结果给出最低限度的充分解释。在这儿,研究目标并非建构或检验更加一般性的理论,而是就事论事提出一套(最低限度的)充分解释,其研究抱负是以个案为中心而非以理论为中心。这一区别反映了许多定性学者以个案为中心的研究抱负,与诸如采取折中立场进行理论化工作(以个案为阵地和中心)和实用主义研究策略这之类的话题上日渐增多的文献中的主张两相呼应。解释某一个案的结果通常要求将不同机制折中结合,这些机制有些是就事论事的(case-specific)或非系统性的(参见第2章和第4章)。
我们在此并非纯粹为分类而分类。相反,通过鉴别三种变体,我们能把我们所做的向我们所说的看齐,这些区分对研究设计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涵,而如果我们把过程追踪当成单一方法的话,这些方法论意涵就被遮蔽掉了。
如何区分过程追踪与其他个案研究方法
综上所述,可以通过作出的推断类型把过程追踪法与大多数其他少量( small-n)个案研究方法区分开来。过程追踪试图在单一个案研究中对因果机制的出现/缺失作出个案内推断,而大多数少量个案方法则试图就因果关系进行跨个案推断(cross-case inferences)。这些不同的推断雄心要求不同的推断逻辑,从而导致了根本不同的方法论(参见第5章)。
有些个案研究方法也能作个案内推断,过程追踪法最突出的替代品就是乔治和班尼特所称的“一致法”(congruence method)。在一致法中,基于自变项(X)的取值,研究者检验依据理论对结果的预测,是否与个案中的发现相一致,无论调查是依时间变化的还是跨(诸)结果各方面变化的。
一致法通常被用以构造一个历史过程的叙事,检验X和Y在一个经验过程的不同时间点(to,t1,…,tn)上的预测值。“除了在因果过程的每一步都呈现相关性的信息”,这类叙事个案研究“可以将这些步骤处境化,使整个过程可见,而不是将其分解到各个分析阶段”。例如,坦嫩瓦尔德对核禁忌的研究涉及一致个案研究,她调查了被测度为“禁忌言论”的X(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的规范)或被测度为“物质主义论点”的Z(物质因素)各自可观察到的意涵是否出现于美国政府的决策过程之中。她用了四个使用和不使用核武器的个案历史叙事,发现在三个核武器几近被使用的个案中,禁忌言论的出现(X)和不使用核武器(Y)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
把一致法和过程追踪法区别开来的关键在于明确聚焦于调查因果机制。一致法调查X和Y之间的相关性,而过程追踪调查有助于产生某一结果的某一或各种机制的运作。过程追踪法超越了相关性,试图追踪把X和Y联系起来的理论上的因果机制。
与鲁巴赫等人的观点相反,过程追踪个案研究通常不能以叙事形式呈现。尽管以事件或时序形式呈现的证据,在根据预测的可观察到的影响类型来检验因果机制的某一部件出现时可能是适当的(参见第6章),但其他类型的证据,如模式证据(例如由不同机构生产的文件的数量),则可能在检验该机制的其他部件时才是适当的。因此,过程追踪个案研究通常应作为因果机制每一部件的逐步检验(a stepwise test)加以呈现,理论检验型变体尤其如此。例如,欧文对民主和平机制的研究就是作为对其理论化机制每一部件的一步步检验呈现出来的,而不是以该个案中事件的叙事方式写成的(参见第5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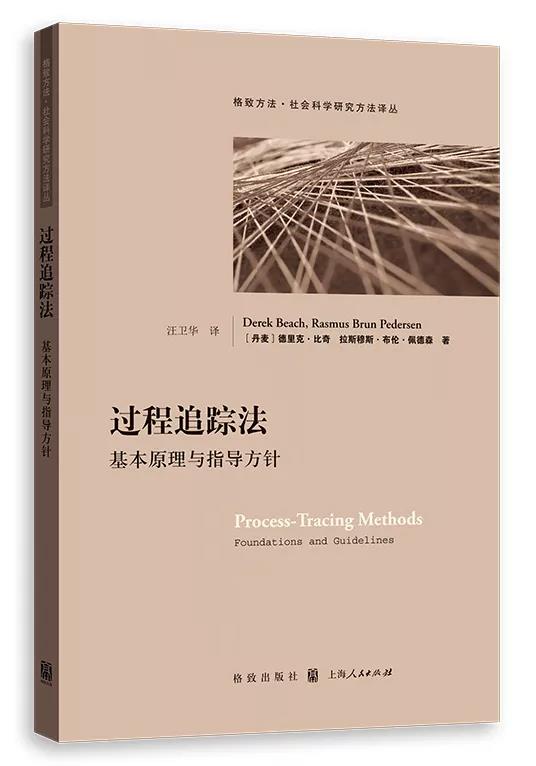
《过程追踪法:基本原理与指导方针》
[丹麦] 德里克·比奇 拉斯穆斯·布伦·佩德森 著
汪卫华 译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社会科学中的过程追踪研究的是将原因和结果联系起来的因果机制的方法。它使研究者能够就一个原因(或一组原因)如何产生一个结果形成强推断。德里克·比奇和拉斯穆斯·布伦·佩德森介绍了过程追踪的精炼定义,将其分成了三种变体,并解释了每一种的应用和局限。作者阐明了过程追踪的隐含逻辑,包括应当如何理解因果机制、贝叶斯逻辑如何使个案内强推断可行。他们为确定最适合手头研究问题的过程追踪变体提供了指引,并为研究过程中的每个阶段设立了一套基本方针。
作者简介
德里克·比奇 丹麦奥胡斯大学政治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欧洲政治、美国政治、国际组织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拉斯穆斯·布伦·佩德森 丹麦奥胡斯大学政治学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欧洲政治、定性研究方法、丹麦政治和国际组织。
译者简介
汪卫华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比较政治学专业主任,北京大学陈翰笙世界政治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政治、中国政治及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