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我思考了很多有关移民的问题,也写了一些文章。今年秋天之后,日本是否应该接受移民的课题很可能会成为日本政治的焦点之一。
现在,我开始越来越实际地感受到日本人口数量的减少。在地方城市,以前热闹非凡的商店街变得冷清下来。由于顾客数量减少,很多商店无法继续经营,被迫关门停业。整个城市变得像是一座鬼城。暂且不说地方城市,我父母家位于横滨市郊外的住宅区,我从小在那里长大。现在他们已经70多岁了,我会时不时地前去看望。街道上已经看不到孩子们三五成群地玩耍的身影了,走在街上的大多都是像我父母一样的高龄者,有的是在散步,有的是去购物。少子高龄化的结果就是人口数量减少,这已经是一个日益紧迫的问题。从理论上来看,围绕着“是否应该接受移民”展开讨论也就成为了一种必然。
谈起移民问题时,如果从老龄化、财政、民族感情、治安等方面进行详细分析,那么要讨论的内容就太多了。但通过归纳不难发现,这些实质上就是一个问题:日本是打算成为一个“大而强的国家”,还是一个“小而富的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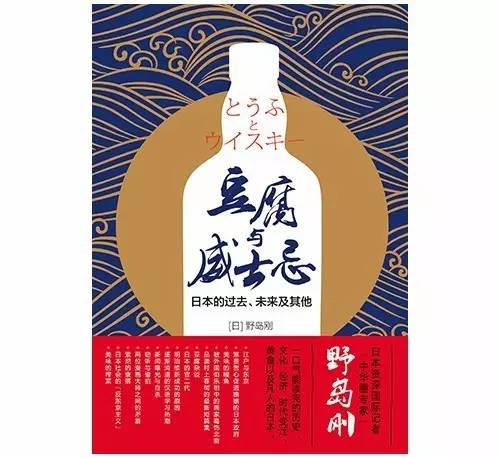
对于生活在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对人口数量已经没有什么实感的中国读者来说,这可能会很难理解。大家也许会认为,日本的人口才1亿多,根本谈不上这些问题。
可是,一旦政府掉以轻心,这1亿多的人口可能会瞬间减少到5000万。其实,增加与减少人口都不是件难事。如果保持目前的出生率,那么日本人口会在2060年减少到现在的2/3,成为8000万。其中,15岁至70岁之间的劳动人口将仅有4000万。
最近,我听说了这样一件事:拥有数百亿美元庞大资产的国际投资基金正在犹豫是否应该在日本进行大规模投资。目前,他们正准备收回一部分投在中国的资金。由于中国未来的经济走向已经逐渐明了,投资基金将减少在中国的投入。但是,是否应该在新的投资对象中加入日本,成了摆在他们面前的难题。
日本政治安定,企业财务状况良好而透明,法律与制度十分完善,非常适合进行投资。但是,投资基金都有一条原则:“不在人口减少的国家投资。”
人口减少会导致国力下降,致使经济总量下滑。虽然国民生活是否富裕要另当别论,但经济总量一旦下滑,经济规模就无法扩大。这样一来,就很难通过投资来得到高效的回报。
安倍经济学的第三大要素是“成长战略”。这关系到日本要如何吸引投资,并促进产业的活性化。为了成功实现这一战略,日本要把自己国家的美好前景向外界展示出来。
安倍政权考虑采用的对策是接受1000万人的移民。如果每年接受20万移民,那么在50年之后,就能抵消掉人口减少1000万所带来的影响。如果这个政策真能落实,将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但是问题在于,把日本建成一个“大而强的国家”之理念,在日本人中间尚未形成共识。
在当今的日本人身上,我们看不到那种积极前往世界各地进行商务贸易的意欲,在国外留学的人数也在逐年减少。国内的年轻人也很少享受奢侈的美味,购买高档产品,或是积极进行消费。在这样的日本社会中,安倍政权的移民政策到底能否实现,将是引人关注的焦点。
外一篇
“爱哭”的日本人
眼泪共分三种,一种是为了防止眼干而分泌的眼泪,一种是异物进入眼中时反射性流出的眼泪,再有就是感情所带来的眼泪了。
我经常会流泪。特别是在看电影、读小说时,一不留神就会泪流满面。和我一起看电影的人经常会被我哭泣的样子吓到。但是,我并不会因为人际关系而落泪。年轻时,即使是被女友甩了,我也没有哭过。
关于哭泣的行为,达尔文进化论认为,眼泪是生物在进化的过程中遗留下来的产物。海洋生物走上陆地后,为了适应陆上生活,就要保持眼睛湿润。因此,人体保留了泪腺这一器官。据说,眼泪的成分与在身体中流动的血液非常相似。
达尔文并不认可眼泪的重要性。他认为,因感情而流出的眼泪只是人类在幼儿阶段尚未掌握语言时,通过“非语言”的形式来表达感情的方式。随着一天天长大,孩子哭泣的次数会逐渐变少,这是他们掌握了语言、能够借其表达自己感情的结果。
没错,达尔文的观点是:“哭泣是一种退化。”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让我开始相信这种理论。
在日本关西地区的兵库县,一名议员被曝挪用公款。他在记者会上嚎啕大哭了几十分钟,一直辩解说自己没有做坏事。这段视频的点击率在网上也一路飙升。
有意思的是,国外媒体把这名嚎啕大哭的县议员当作了“爱流泪谢罪的日本人行为的象征”。
外国人常说日本人面无表情,不会把感情展现在表情和动作上。欧美人甚至还说:“日本人就像是戴着面具一般面无表情。”但是,欧美人反而不会在公共场合流泪,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无法控制自己感情的表现,是件非常丢人的事情。而在日本,人们往往不会去责备在公共场合哭泣的行为。不仅如此,这种行为还会被认为是一种发自内心地反省与谢罪的表现,有时能够博得人们的同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