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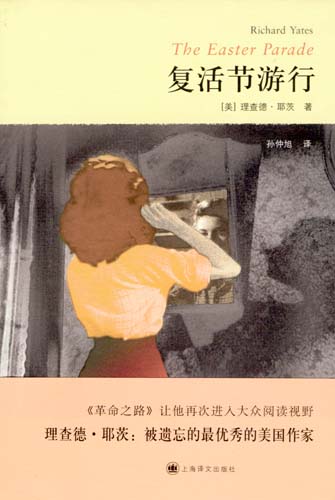 值得仔细研究的是孙仲旭翻译的三十多本书的名单,我们会发现,名单中仅有一人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奈保尔。但其中好几位作家的翻译难度要高过诺贝尔文学奖作者的平均水平。所以,这是耐人寻味的一个指标。这些书目就是他的视野与版图。这是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这是他在为我们聚焦。 值得仔细研究的是孙仲旭翻译的三十多本书的名单,我们会发现,名单中仅有一人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奈保尔。但其中好几位作家的翻译难度要高过诺贝尔文学奖作者的平均水平。所以,这是耐人寻味的一个指标。这些书目就是他的视野与版图。这是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这是他在为我们聚焦。
德里达制定过“友谊的法则”:一个朋友总要先死在另一个朋友的前面,幸存的那个朋友就有了埋葬和悼念死者的责任。因此,友谊与哀悼就这样不可分离。
此刻,不存在说话合适的可能性—谁能说出合适的话来?但在所有不合适的话中,有些话是最不合适的。比如,完全没有医学专业背景的人侈谈抑郁症的诊治、用微信了解到的翻译稿费去测量伟大灵魂的深度、从没翻译过一万字的人畅论翻译的苦楚与艰辛……
在E. B. 怀特的《从街角数起的第二棵树》一书后记里,孙仲旭说他“深为怀特文字的精雕细琢、富于情趣及识见的不凡而打动。”“有幸接下本书的翻译任务,终于圆了译一本怀特作品集的夙愿。”
也就是说,孙仲旭翻译外文书,稿费至少不是考虑的首要因素。退一万步说,没有稿费,诗人也还在写诗。
没有一分钱,还是有大量的人在钓鱼、跑步、爬山、游泳……有人会说,那些是对身体有好处的,而翻译却损坏身体。那网络游戏呢?
值得仔细研究的是他翻译的三十多本书的名单,尽管书目有可能是他和出版社磋商、妥协的结果,但仍然可以感觉他的喜好、见解与战略。我粗略将他的译作分类如下:
一部分是长销书,如奥威尔、塞林格、卡佛、奈保尔、怀特、伍迪·艾伦、林·拉德纳。
一部分是文艺书籍:普拉斯、斯托帕、格罗史密斯、麦克尤恩、耶茨、麦卡利斯特、麦克纳尔蒂、詹姆斯·瑟伯、雪莉·杰克逊。这些文艺书籍中,有些可能会变成长销书。
此外还有些偏实用的书,如玛格丽特·亨利的经典童书、艾拉·雷文的惊悚小说、关于流行音乐的书籍。值得提一下艾拉·雷文,他的《死亡陷阱》是百老汇上演时间最长的惊悚舞台剧。
我们会发现,名单中仅有一人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奈保尔。但其中好几位作家(如伍迪·艾伦与怀特)的翻译难度要高过诺贝尔文学奖作者的平均水平。难度不代表文学水平,但会与译者的劳动强度挂钩,与销量可能反向挂钩。所以,这是耐人寻味的一个指标。
难度还存在于普通读者意识不到的地方。比如说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因为已经有了施咸荣的译本,后来者想要取而代之比较难。一是施咸荣的爱好者会有先入为主的看法,二是有的读者不觉得此书有读两个译本的必要。比如我。
几乎所有的读书人都知道何伟的《寻路中国》,此书2011年问世后变成了畅销书,说它是报道中国最好的新闻作品也不为过。
同样是在《纽约客》上发表的文章结集,孙仲旭翻译的《门萨的娼妓》就没有那么幸运了,2004年问世后却不大有人知晓,至少影响力和《寻路中国》没法比。
但纯粹就智力劳动的成就上,我觉得何伟与伍迪·艾伦难分轩轾。在翻译的难度上,《门萨的娼妓》可能要难5倍。全中国能翻译这本书的人不会超过10个。中英文俱佳的人也是有的,但熟稔美国文化、对伍迪·艾伦的冷幽默能会心一笑的人就不多了。
孙仲旭选择比较难的书来翻译,看中的是书的价值。
当然,有些书翻译难度并不大,但也都是好书,甚至是必读书。这种眼光与气度就比较少见了。
国内有一批只读“好书”的读者,他们只读也许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著作。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会发现发达国家的读者的知识面要比我们宽广很多。比如说关于抑郁症,我们的知识与宋朝人差别并不明显。假设一个穿越过来的宋朝人,看半个小时的网页,就基本上与我们持平了。这些年追看过美剧的人,应该发现柏拉图说得真对:知识就像是一个球,球内是已知的,球外是未知的,你知道越多,就发现自己不知道的更多。
一个人,读遍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者的书,他未必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完整的人。而当今世界精神领域创造的核心,无非是那几百本书。好莱坞大片、日本漫画,以及最新的时尚,都围绕着这个核心在转动、变幻。
这些书目就是他的视野与版图。这是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这是他在为我们聚焦。
在书目中有一本《塞林格传》,这是他翻译的第一本书,他的评语是“我出的第一本译作,现在很不满意,建议不要读。”
将半真半假的笑话放一边,我们会发现孙仲旭的战术是清晰的:先翻译传记,再攻打《麦田里的守望者》。在国内翻译界,这是最先进的战术了。
孙仲旭,一个可信的译者,因为可信,也许将来还会是一个出版的品牌。有质有量的译者,孙仲旭之外,还能推荐一个人给我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