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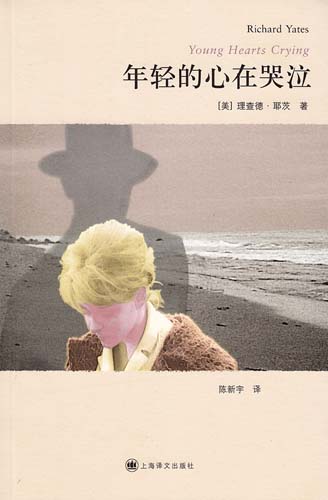 忽忽2011年归入历史了,《书缘》版将一连三期盘点过去一年小说类、人文社科类、财经类引起书界关注的部分书籍,尽力不为铺天盖地的宣传所囿,而是腾出更多位置给那些静处一隅却值一读的作品。 忽忽2011年归入历史了,《书缘》版将一连三期盘点过去一年小说类、人文社科类、财经类引起书界关注的部分书籍,尽力不为铺天盖地的宣传所囿,而是腾出更多位置给那些静处一隅却值一读的作品。
从浩如烟海的出版物中挑选出若干本所谓的年度好书,不是易事,也未免鲁莽。毕竟,阅读更多时候是一种个人行为,对于读者而言,怎样的书才是好书,别人说了不算,惟有自己去阅读。我们深知所能提供的,仅仅是一份参考,当然,我们希望这是一份有价值的参考。
——编者
盘点2011年小说类作品,不得不提张大春的《城邦暴力团》。武侠小说的外套里头藏着的是一连串亦真亦假的历史秘闻。
地下社会与特务统治如何互为一体?蓝衣社、武功秘笈与神秘失踪的佛头缘何纠缠一处?淞沪抗战、桐油借款、黄金运台又究竟有多少不为人知的隐情?张大春将中国小说叙事技巧与稗官野史传统巧妙结合,一步步揭开近百年来中华民族风雨史背后的秘辛。
我鼎力推介此书不全然因为该书穿越在正史与轶闻之间的大胆妄为,抑或张大春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垦拓了武侠小说的新疆界,而是《城邦》中凭空而造的各种纷乱锦绣的知识典故,从奇门遁甲、巫卜星相、书法画论乃至美食细典、格斗技法。
在向来接受的文学教育里,小说通常只是一种虚构性文体,故事、情节、人物为判断一本好小说最重要的指标。小说当然可以涵盖知识,但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知识”或纯为日常生活的常识、或为小说推进的必要桥段、或为凸显人物性格的补充说明,换言之,小说中的知识少有一己独立的地位和美学价值。那些在前贤看来毫无不妥并且津津乐道的细琐典掌到了今天,却被自动抽离出我们的文学教育。就此而言,《城邦》真正打动我的就是张大春有心有力以小说的花招自觉洗发刮磨出那些沉溺历史底端的知识。当这些充满中国味道的知识进入小说,它便不是一本今日大多数作家的那种用汉字写就的“西方小说”,而是有了自己的中国根脉。
同样恢诡炫奇的是韩松的科幻小说《地铁》。该书的写作指涉出一个习焉不察的事实,每年,相当于全国城市人口总数三分之一的人,在这地下作封闭式旅行,说地铁是一个忽然出现的崭新国度并不夸张。
黑暗而陌生的领域、突兀充满金属感的比喻、一力开显当下生活真实的用心、碎片化的叙事方式,韩松给予我们迥然不同的阅读体验。与刘慈欣那种波澜壮阔到能将我们带出地球表面的科幻小说不同,韩松毋宁说是要把我们拖入地下,不仅物质层面的地下,更从家国到个人的精神地下。作为一名记者,他从白天观察中国的思考者,到夜晚经由超现实的方式记录他所看到的当代中国,最终用小说的曲笔写就曲笔的现实。
我非科幻迷,无力细致描摹韩松小说中那种时刻迸发的错杂快感,我只想作一小小的提醒,刘慈欣的《三体》系列与韩松的《地铁》或许无意间回应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不要忘了在1903年,彼时留学日本的鲁迅先后翻译了两本小说,一为《月界旅行》,一为《地底旅行》。当我们今天谈论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时,不能忽略鲁迅是以科幻小说的想象与翻译介绍为其文学之始的。然则不论鲁迅,还是今日的刘慈欣、韩松,亦不论到底是冲向月界还是钻入地下,共同点与重点皆为他们面对当下的种种无奈,企图通过文字的想象力去创造一个个纸面乌托邦。
如果说张大春的《城邦》意在诘问历史与现实的暧昧分际,韩松的《地铁》探寻隐而不彰的生活领域,那么2011年4月间推出的张爱玲《雷峰塔》、《易经》则将我们带回个人内心世界最不为外人道的角落。
继《小团圆》出版后,不难发现张爱玲反复重述生命中最晦涩难言的心事,但每次出手均以不同的角度、方式,极致细腻地铺写她对周遭不同人事物的爱恨情结,让人读来更知那个临水照花人原是这样。
按弗洛依德的说法,一个人毕生都在演绎他儿时的梦想,而美国小说家薇拉·凯瑟则说作家经营的根本素材大半是十五岁之前耳濡目染之默化阴孚,清绝孤傲如张爱玲亦不免上述说法。
《雷峰塔》里小琵琶走亲戚,去二大爷家,张爱玲感慨:“现在由富贵回到贫困,这一家人又靠农夫的毅力与坚忍过日子。年轻人是委屈了,可是尽管越沉底的茶越苦,到底是杯好茶。”可她偏偏要搅动一番这杯陈年苦茶。相较《小团圆》,这回她更直接地写出与母亲复杂紧绷莫名难宣的心事与痛事。美丽飘忽的母亲对她永远“失望”,小到宴客搬椅生过节,大到《易经》里要骂出声,母女隔膜在在可见,“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的毁了我的爱。”母亲张扬厉害,女儿相似的强悍,外加从小玲珑肚皮里做功夫,自然互不见容。这般纠葛的母女关系成了张爱玲毕生的情感十字架,甚至母亲病重之际,她寄上关于自己的评价资料,大约也无非为了证明自己,讨母亲一句夸赞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