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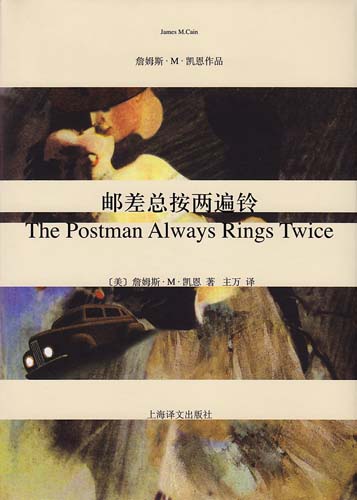 说起来很惭愧,这一年书看的少,新书更少。旧书倒是常拿出来翻翻。这么着,排行榜和出版社都不干了,可是,读书不是因为合心意才去看吗? 说起来很惭愧,这一年书看的少,新书更少。旧书倒是常拿出来翻翻。这么着,排行榜和出版社都不干了,可是,读书不是因为合心意才去看吗?
金克木先生的《书读完了》(上海辞书出版社)是常常拿出来翻的。这是一本写给普通读书人的秘笈,而且是一本有着奇特生命力的书。一篇篇文章,是一个体力已经不那么充沛的老头恨不得要把满心满腹的话一股脑儿地说出来,可又不能明说和全说,所以悬疑,所以善巧,勾引着人去看,连书名也是。
它绝不是知识点的检索,也不是玩弄文字的小乾坤,而是透着清澈和明亮,我能感觉到老先生全部的善意、智慧和彻底“利他”——他的心里头是面对听众的。无论读书多少,我还是要回到这本“读完的书”来矫正一下位置。今年出了《金克木全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善莫大焉。有了这本秘笈,有多少书可以不读,有多少人与事是可以“浮云”呢。
按照老先生的指示,像我这样既想“排毒”又想“养生”的,就有了一条便捷门径。《老子注译及评介》(陈鼓应著 中华书局),《庄子今注今译》(陈鼓应注释 中华书局),《论语译注》(杨伯峻译注 中华书局),《周易译注》(周振甫译注 中华书局)等都是可以方便找到,且是行文干净的入门书。
虚构小说,有影视的衬托往往不坏。想必,随着Life of Pi(Yann Martel)的电影拍成,《少年Pi的奇幻漂流》(姚媛译,译林出版社)会梅开二度。小说《邮差总按两遍铃》(詹姆斯·M.凯恩著,主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也就是个中篇或小长篇,曾经四次被搬上银幕,现在有了干干净净的译本。作为黑色文学或电影鼻祖,小说本身就像影像白描。
极简主义的风格,无论装修还是文字,容易被兑水成寒碜的简单。此前,理查德·耶茨的作品《复活节游行》(孙仲旭译)和《十一种孤独》(陈新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也是因为电影《革命之路》才开始被关注。故事的主人公往往境遇孤独凄凉,人间冷漠尽收眼底,因此读者一直不待见。借光大明星,作者身前的落寂突然有了回声。雷蒙德·卡佛的作品也是被自己的出版编辑删成了极简,无论中英文都好读,况且还有译者小二自发的热爱去翻译。
J.D.塞林格《九故事》(李文俊 何上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是把天才、隐士和“萝莉控”嫌疑人“水溶于水”。斯蒂格·拉森的千禧年系列《玩火的女孩》(颜湘如译,人民文学出版社),是用生命实践来写作。《鸟看见了我》(文化艺术出版社)的作者阿乙则试图从热腾腾的现实里把住文学这根脉。到了非虚构写作这里。彼得·海斯勒用训练有素的、旁观者的冷静口吻说出了他的观察与忧虑《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上海译文出版社)。他已经离开中国,可是这土地上生活的人和与之有精神纽带的人总不会一走了之,水泥垃圾也得消化。中国媒体往往在非虚构写作这里有引人入胜的不俗表现。
《三十三年之梦》、《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和《孙逸仙传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是精心选择的辛亥百年纪念读物,当事者的回忆和编纂,读来非常有质感。对那一段血雨腥风和覆巢之下几无完卵的历史大动荡、思想大纠结和大颠覆,确实值得一窥。
《朝觐东方:理雅各评传》(吉瑞德(美)著,段怀清、周俐玲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从一个英国传教士理雅各到牛津汉学家的身份转变历程折射出一段中国历史,更是从学术角度对人性的切入,可作为另一种样式的自传。同一出版社的《欧洲思想史》(弗里德里克·希尔(奥地利)著,赵复三译)虽不是新书,却是重要的思想体系参考书,能让人感觉到思想之流动,是一本同样有生命的大书。这本著作完成于1953年,初稿在希特勒执政时被纳粹政权没收;1946年又被苏联占领当局没收,第三次撰写,作者是在抑郁和病痛之中完成,乃今日所读。
《特朗斯特罗姆诗全集》(李笠译,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竟然也有十年了。据说媒体记者每年公布诺奖的时候都在特朗斯特罗姆家门口守候,今年懒得蹲了,算是冷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