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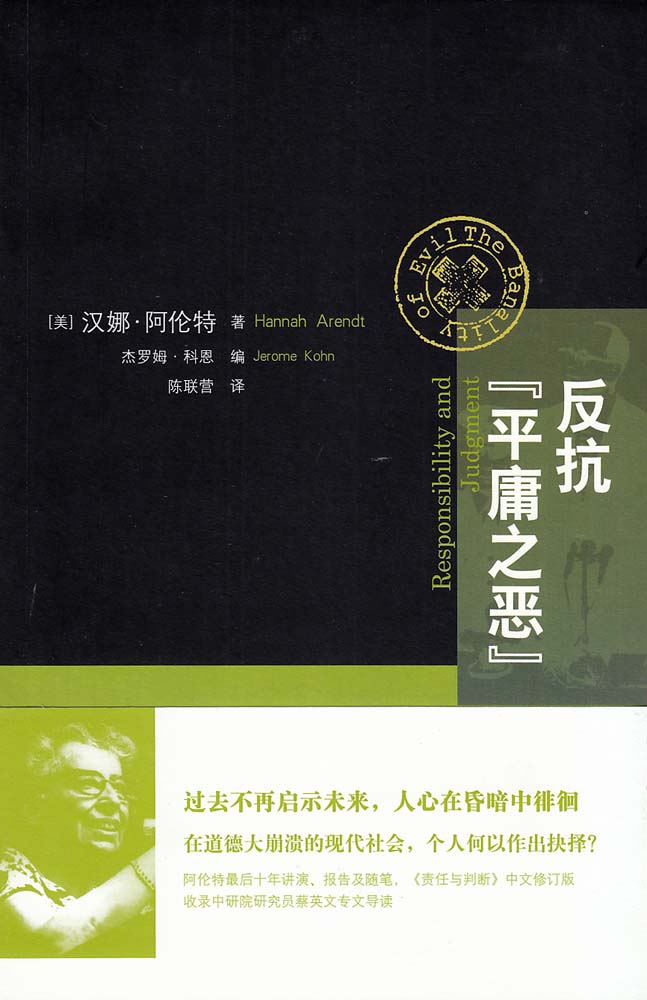 首先,我想对由《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所引发的那场相当激烈的争论作些评论。我故意说“引发”,而不说“造成”,是因为这场争论大部分针对的是一本子虚乌有的著作。所以,我的第一反应是用那位著名的奥地利智者的话来打发这桩事:“再没有比关于一本谁都没读过的书的讨论更有趣的事了。”然而,随着事态的发展,特别是在后期,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不仅以我从没有说过的话来攻击我,而且竟还有人为此而为我辩护,这时我逐渐明白,这桩有点儿奇异的事情比单纯的感情用事或玩世不恭要更复杂。在我看来,事情所包括的也不仅是“情绪”了: 不仅是在某些情况下确实会中断作者与读者之间交流的那种坦诚的误解,也不仅是那些利益集团的有意曲解和伪造,因为这些利益集团更害怕一场针对那个时期的公正而仔细的调查被引发,而非我的书本身。 首先,我想对由《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所引发的那场相当激烈的争论作些评论。我故意说“引发”,而不说“造成”,是因为这场争论大部分针对的是一本子虚乌有的著作。所以,我的第一反应是用那位著名的奥地利智者的话来打发这桩事:“再没有比关于一本谁都没读过的书的讨论更有趣的事了。”然而,随着事态的发展,特别是在后期,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不仅以我从没有说过的话来攻击我,而且竟还有人为此而为我辩护,这时我逐渐明白,这桩有点儿奇异的事情比单纯的感情用事或玩世不恭要更复杂。在我看来,事情所包括的也不仅是“情绪”了: 不仅是在某些情况下确实会中断作者与读者之间交流的那种坦诚的误解,也不仅是那些利益集团的有意曲解和伪造,因为这些利益集团更害怕一场针对那个时期的公正而仔细的调查被引发,而非我的书本身。
这场争论总是提到各种纯粹的道德问题,其中有许多我从没碰到过,而其他一些我也只是捎带提及。我对审判作了一个事实性的叙述,在我看来,甚至这本书的副标题——一份关于恶的平庸性的报告——也是从我认为不需要进一步解释的案件事实中明确地得出的。我指出了一个因与我们关于恶的理论相龃龉而令我震惊的事实,因此也就指出了某种虽真实但看起来不合理的东西。
我有点儿想当然地认为,我们仍然与苏格拉底一样,相信受冤枉要比作恶好。这种信念被证明是一个错误。人们普遍相信:人不可能经受任何诱惑;在关键时刻,没有一个人值得信赖,甚至没有一个人可以被期望是值得信赖的;被诱惑与被胁迫几乎是一样的,而用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她首先发现这个谬论——的话来说:“如果某人用一把手枪对着你说,‘杀了你的朋友,否则我就要杀了你’,他是在引诱你。就是这么回事。”尽管生命处于危险之中这一诱因,可以是使一个人免于遭受惩罚的合法借口,但它肯定不能被道德正当化。最后并且最令人奇怪的是,我们处理的是一个其结果必定是要得出某种判决的案件,我却被告知下判断本身就是错误的: 任何不在场的人都不能下判断。顺便说一下,这也是艾希曼自己反对地方法院判决的理由。当人们告诉他当时有其他可选办法,而他也本可以避开履行他的谋杀义务时,他坚持说,这些只是产生于后见之明的战后神话,是那些不知道或已经忘记实情如何的人们所迷信的神话。
关于判断的权利和能力的讨论,之所以触及了最重要的道德问题,原因有很多。这里涉及两件事情: 第一,如果大多数人或我的整个周围环境已经预先判断了某个事件,我如何还能分辨是非?我是谁,有什么资格去判断?第二,如果可以的话,在何种程度上我们能判断那些自己并没有亲历过的事件?就第二点来说,如果我们否认这种能力的话,看来明显的是,任何历史编纂和法庭程序就都是不可能的了。可能有人会更进一步主张,在那些我们运用判断能力的事例中,很少是不通过后见之明来判断的,而这对历史学家和法官同样真确,法官确实有理由不相信目击者的叙述或在场者的判断。此外,因为这一不在场者的判断问题通常伴随着傲慢的控诉,所以,谁还能声称,去判断一桩不义之事,就预设了自己不会犯下这同样的罪行?甚至一个谴责杀人犯的法官仍可能会说,要不是上帝的恩典,我可能也会走到那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