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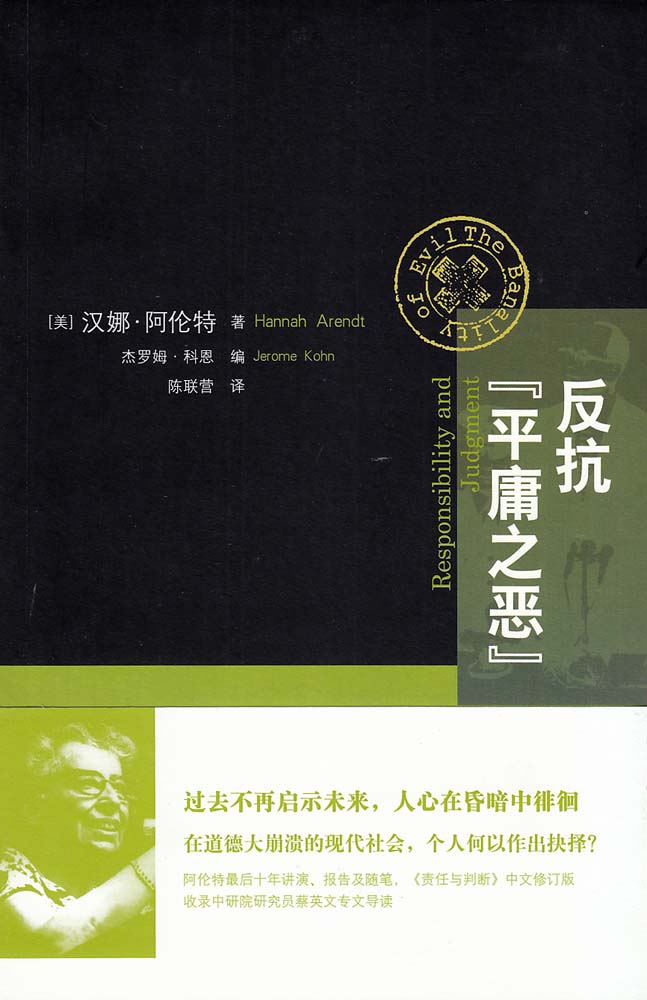 一 一
1960年5月11日黄昏,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外贫民区,三个男子瞬间挟持了一位刚从公共汽车上下来的五十多岁的男子——阿道夫·艾希曼。绑架者们未用过分的暴力,也未使用武器威胁,但被绑架的这位德国党卫军中校马上意识到自己已落入老练的以色列特工的手中。十天后,艾希曼被偷运出境抵达以色列。阿根廷政府向以色列政府提出了“侵犯阿根廷主权、法律”的外交抗议,以色列政府则以艾希曼犯有“史无前例的屠杀了欧洲六百万犹太人”重大罪行为理由,强调劫持行为和以色列法庭审判艾希曼的正当性。
二战中,德国党卫军公安部与盖世太保、秘密警察等各种警察机关合并,成立了国家公安部(RSHA),国家公安部的第六局第四科为犹太人问题科,因所负使命“重大”,直接听命于希姆莱和海特利希的指挥。当时处理犹太人的各种行动大都是艾希曼直接负责。因为由以色列法庭而不是国际法庭审判逃亡在海外的纳粹罪犯属于史无前例之举,所以,耶路撒冷的这次审判举世瞩目。1961年4月开庭审判,同年年底一审法院下达了死刑判决,1962年3月二审开始,5月底驳回被告上诉维持原判,5月31日对艾希曼执行绞刑。
艾希曼被捕的消息震动了整个世界,受冲击最大的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阿伦特严肃指出,因为“至少这种对直接杀人犯的认真、努力的审判,还是第一次”,“至今德国人对当年屠杀犹太人的结果不甚关心,杀人者即使自由地昂首阔步地走在公共场所,也没有人给予特别的注意”。战后西德一万一千五百名司法官员中约有五千人在纳粹执政时期担任同类职务。不仅司法界,联邦及各州政府部门、警察机关、大学、公共团体中身居高位的旧纳粹政权要员也不少。如党卫军高级干部马丁·菲伦茨还是自由党中坚干部,艾希曼被捕后,他在德国锒铛入狱,被检察院起诉,结果法院只判四年徒刑。1958年西德虽然设立了追查纳粹罪犯总部,但因为缺乏检举的“人证”、“物证”,实际上不过是敷衍社会、世界舆论的一种举措。尽管许多纳粹罪犯及其犯罪证据都曾在媒体上公布过,他们也未曾隐姓埋名潜入地下,而且也未超过法律所规定的二十年内追溯的时效,但1958年至1963年间,在一百二十名战时犯有杀人、协助杀人罪行的被告(内不少是党卫军高级军官)中,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仅二十九人。地方法院对许多犯有滔天大罪的纳粹党徒都作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轻微判刑,如参与夺取四万犹太人生命的奥托·勃拉特菲歇博士仅判十年徒刑;曾任艾希曼法律顾问的奥托·法拉齐在战争结束前强制移送了一千二百名犹太人,并“解决”了其中的六百余人,仅判五年徒刑,而且不剥夺公民权。战后不少在欧洲其他国家被判处死刑的纳粹罪犯,如在西德法庭受审的话,不仅生命无虞,还处以极轻的刑罚。在西德,很多杀人多达三位数不足四位数的罪犯都被判处“无罪”。
艾希曼被押到以色列受审时,西德媒体也承认德国社会处于一种尴尬境地:“如果艾希曼引渡到西德会导致重大的政治危机,他会因无杀人意图而被释放。”本来艾希曼被用绑架的方式押到以色列审判在国际上是有争议的,他仍拥有西德国国籍,作为保护本国海外公民权利的西德政府有理由提出引渡要求。但是,司法界只有一位高级法官在新闻媒体提出了引渡的观点,因为他是犹太人。他的引渡提案在司法界、新闻界无一人响应,湮没无闻。现实与当时西德总理阿登纳所说的纳粹党员占德国人口比例很低的论点相反,政界许多人“自己身子不干净”,感觉麻木,对清算纳粹分子罪行不感兴趣。
阿伦特在她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对德国社会提出尖锐的批评。她说,从种种证据看来,只能下这样的结论:能说成良心的那种良心正在德国消失,德国国民连良心的存在都忘记了。但是,阿伦特在书中也记叙了德国国民闪光的历史记录。犹太人考乌纳尔在审判艾希曼法庭上作证:1941年春德军安东·歇米特上士担任波兰战场的收容伤兵任务时,通过犹太人组织负责人考乌纳尔为犹太人逃亡提供伪证件和军用卡车,特别重要的他不是为了钱。半年后歇米特被捕、处死。当考乌纳尔讲完歇米特上士的事迹时,全场鸦雀无声,法庭的听众自发地为歇米特这个名字默哀两分钟,“这像是漆黑一片中闪出的两分钟的光芒”。
以色列政府也有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如果追究残酷杀害六百万犹太人罪行的话,那么,当年德国各级政府、国防军、参谋本部乃至司法界的官员都对“最终解决”犹太人应负相当的责任,但这是个高度敏感的问题,超出一定范围将涉及德国全体国民共同犯罪的问题。所以,以色列检察当局取“慎重态度”。这次审判表面上是纯粹的不受政治影响的司法审判,实际上在中东陷于孤立的以色列受到西德经济援助,为了保持这种以德关系,审判也不是无条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