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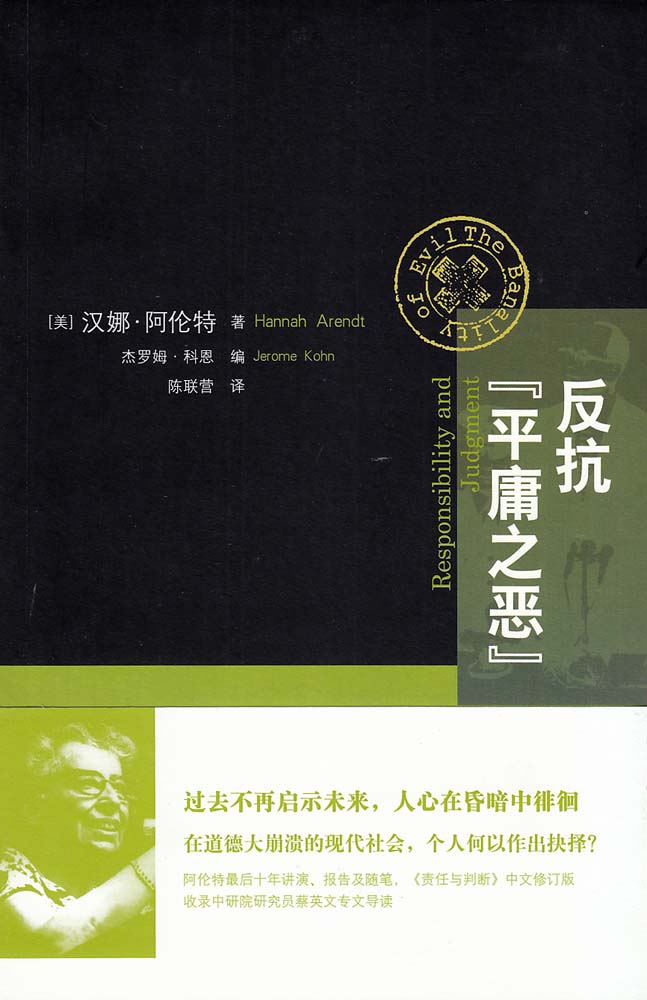 1960年,以色列情报部门查出藏匿在阿根廷的原纳粹德国高级官员、犹太人集中营大屠杀负责人阿道夫·艾希曼的下落,将之迷捕并运回以色列受审。经过审判,1962年6月1日,艾希曼被处以绞刑。 1960年,以色列情报部门查出藏匿在阿根廷的原纳粹德国高级官员、犹太人集中营大屠杀负责人阿道夫·艾希曼的下落,将之迷捕并运回以色列受审。经过审判,1962年6月1日,艾希曼被处以绞刑。
在审判席上,艾希曼为自己作了无罪辩护。他声称自己对犹太人并无仇恨,执行屠杀方案并提出旨在改善执行效率的操作建议,仅仅是在完成上级指派。这种说辞当然迎来了舆论界的猛烈抨击,认为是一派胡言,是在进行徒劳的抵赖,也最终没有被法庭采信。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或者说,直到今天,很多人在评价艾希曼这样的杀人魔头时还是会提出,那是坏到极致、有着嗜血魔性、深受扭曲意识形态左右的狂魔。
很快就有人提出,艾希曼所为并不鲜见,他的罪行不容饶恕,但之所以会犯下如此惊人的罪行,不是因为艾希曼这个人特别有别于常人,而是普通人的“平庸之恶”在特定机制和环境下发挥到了极致。也就是说,没有艾希曼,仍然会有其他人去做屠戮犹太人的事。
这番观点一经提出,就迎来了不绝的骂声,认为是在为纳粹狂魔开脱,或者说抹黑普罗大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1980年代陆续解密了斯大林时期的档案,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进一步加速了历史档案解密过程,人们惊骇的看到古拉格等一幕幕惨不忍睹的历史记录,这背后除了政治强人、体制和意识形态的责任,“平庸之恶”也逃不了干系。拉美20世纪后半期长期处于频繁政变和军人干政,进步人士阵营被多次清洗,拉美国家国内国民的“平庸之恶”容忍了政客和军人的施恶,美国国内的一大批自由市场理论经济学家更是对政治恐怖熟视无睹,甚至以为在专制的拉美找到了自由市场经济的绝世乐土。
中国读者更为熟悉的“平庸之恶”历史片段,当然是文革。那段历史中比较知名一点的作恶者,也普遍被视为病态化、受权欲和意识形态驱使的“非常人”,至于更多的常人,都在诉说自己是受害者。
“平庸之恶”观点是对的,这个概念的提出者汉娜·阿伦特成为了论辩的胜出者。但这番观点在流传中,也常常被人有意或无意予以误读。《反抗“平庸之恶”》再版推出,给了我们重新思考的宝贵机会。
服从实验:平庸之恶为什么是可能的?
在讨论《反抗“平庸之恶”》这本书之前,我们不妨先看一下另一本书。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托马斯·布拉斯所著的《电醒人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版)介绍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社会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做过的一项著名社会实验:服从实验。米尔格拉姆1933年出生在纽约的一个东欧犹太人家庭,他于1962年5月27日(艾希曼被处死后的5日前)在耶鲁社会心理学实验室通过实验证实,最普通的美国人,也就是有一定几率成为美国法庭的陪审员的美国普通公民,心智健全且对美国价值观没有任何明显逆反的普通人,在实验中会毫不犹豫地向无辜受害者施加痛苦甚至可能致命的电击。
米尔格拉姆向参与实验的美国公民宣称,举行的是一个记忆实验,要求实验对象对答错题目的“演员”给予电击,强调电击不会带来太大痛苦。实验开始后,多名实验对象对随着电击强度不断增强,而导致的被惩罚对象发出的哀鸣表示出不忍,但在米尔格拉姆要求他们不得半途而废后,继续了下去。米尔格拉姆说,“那是一副令人困扰的景象,受害者拼命挣扎反抗,发出痛苦的哀号……但是他(实验对象)却一脸冷漠,像个机器人一样继续实验……(最后)满意自己正确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
让美国人无法接受的结论出来了:即便是美国人(而不是二战中,以及二战前被纳粹长期洗脑的德国人),也有多数人会轻而易举地服从权威。《电醒人心》书中还写道,有实验对象“很显然不愿继续伤害学生,但是却无法将这种不情愿变成实际行动”。谁说这些实验对象、普通的美国人,在另一个环境下,不会变成艾希曼?谁又能保证今天的我们,在民主、权利、自由、宽容成为口头禅的同时,一定没有成为艾希曼的可能?
当然,米尔格拉姆的实验中,也有部分实验对象没有坚持到最后,中途强行退出电击。《电醒人心》书中归纳了几点因素:实验对象产生了对受害者的移情;主持实验的人漠视实验对象提出的问题或抗议;有多名实验对象同时参与实验,且有人率先站出来提出异议或反抗。米尔格拉姆认为,“当个体想要站在权威的对立面时,如果他所在群体中有人支持他的反抗,那么他就会做到最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