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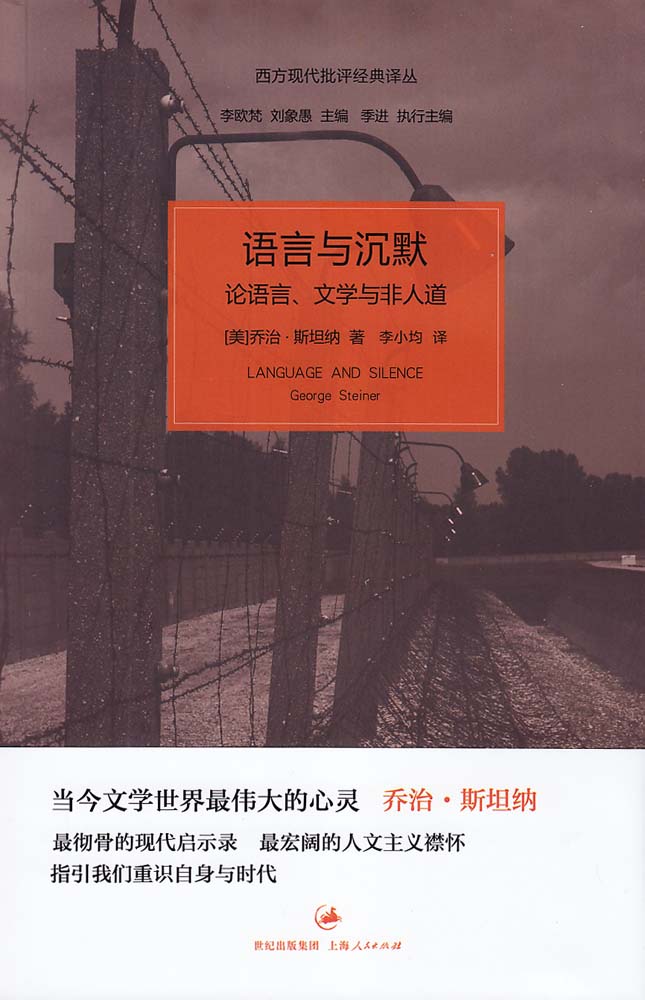 斯坦纳在本书《教化我们的绅士》一文中引用了卡夫卡的话: 斯坦纳在本书《教化我们的绅士》一文中引用了卡夫卡的话:
如果我们在读的这本书不能让我们醒悟,就像用拳头敲打我们的头盖骨,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读它?难道只因为它会使我们高兴?我的上帝,如果没有书,我们也应该高兴,那些使我们高兴的书,如果需要,我们自己也能写。但我们必须有的是这些书,它们像厄运一样降临我们,让我们深感痛苦,像我们最心爱的人死去,像自杀。一本书必须是一把冰镐,砍碎我们内心的冰海。
对我而言,这本书就是一把冰镐,砍碎我内心的冰海。
我要首先谢谢斯坦纳,与大师同行的日子是幸福的。十几年前,读翻译理论,就读过他的名作After Babel,当时只惊叹于他的博学,对他是敬而远之。想不到我居然还有如此缘分:在三十七岁的时候翻译了他在三十七岁时结集出版的文集。
我要感谢季进先生的信任。我生性疏懒,此前只“读其文字,想其为人”。这次受命译事,诚惶诚恐,冀希不辱使命。
在翻译过程中,得到许多师友及学生的关爱,在此一并致谢。特别要感谢邓中良教授、张晓红教授、阮炜教授、刘波教授、吕晶珠博士、李致远博士、李炜先生、肖梅女士、杨旭辉女士等人提供的大力帮助,译事才能顺利完成。
感谢北京世纪文景公司张铎先生。他严谨细致的编辑工作为本书增色不少。
翻译是孤独的事业。在语言的极限地带,是一个人的“战争”。因此,某种意义上,是“抛家舍业”。无论如何,最需要感谢的是家人的理解和支持。
在《两种翻译》一文中,斯坦纳特别欣赏著名的荷马译者菲茨杰拉德的译文:
将来,死亡会从远海袭来,
温柔如雾之手,抚摩你,
值你衰疲的岁月,
富有舒适的晚年。
斯坦纳认为,译者应该把“温柔如雾之手”当成翻译的准绳。对于这样的标准,我虽然“身不能至,但心向往之”。我只是那个卑微的“侍从”,跟随在大师的身后,小心翼翼地牵着他的衣衫。译本中舛误难免,概由译者负责;敬希方家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