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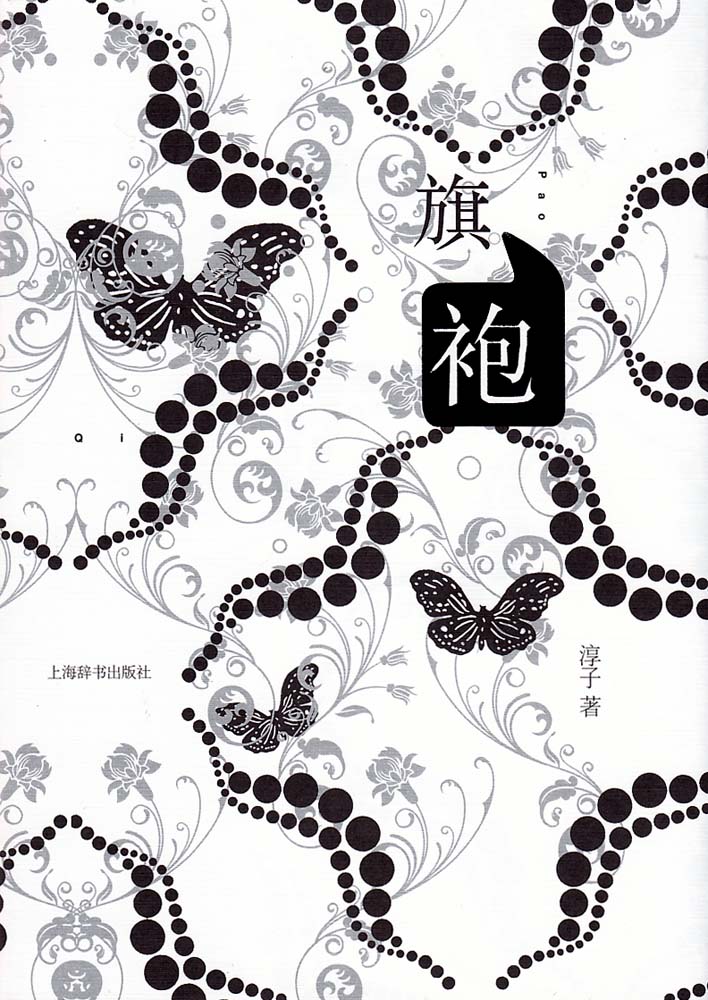 有人说,上海是中国的外国,上海人很多地方与内地人不一样。此话稍稍有点别扭,但是一个基本的事实还是说对了,那就是上海的非凡及上海人的另类。 有人说,上海是中国的外国,上海人很多地方与内地人不一样。此话稍稍有点别扭,但是一个基本的事实还是说对了,那就是上海的非凡及上海人的另类。
这也难怪,上海有过一百多年一市三治的历史,即华界、英租界、法租界三个行政区并存、磨合在一个城市里,五方杂处,华洋并举,西风昌盛……存在决定意识,用熊月之老师的话来说就是:“藏龙卧虎的老上海,于人多、房多、事多中,更突显名人多、闻人多、奇人多、洋楼多、名居多、要事多、趣事多、怪事多的特点。假如你徜徉在衡山路、永嘉路、复兴路的梧桐树下,碰上三个五个轰传海外的名人故居,踩过十个八个来自五洲四海的名人足迹,听到一桩两桩闻所未闻的奇闻轶事,千万不要大惊小怪或欢呼雀跃,这就是上海之所以为上海的地方。”由于上海的海派特性,近些年上海几乎也成了一门显学,像一座开发不尽的富矿,不断地引出发掘老上海、研究老上海的新著。
淳子关注和研究老上海的视角偏重于女性,着力的重点在于名女人内心世界的深层揭示,选择的场景没有一般人笔下大都市的繁华和嚣闹,而是小街小景、小楼小巷、小书房、小阳台……语调沉稳,慢节奏,遣词造句隽智而富有哲理,于是就有了《老房子里,点点胭脂红》、《在这里——张爱玲城市地图》、《旗袍》、《口红》……阅读她的书不能图畅快,不能一目十行,不能边吃零食边看,因为你的目光走不快,你的零食还没有掉进嘴里,你的神思或是情绪,就已经掉进她的语境或者说是“陷阱”里了,动辄就被“磕绊”住了,禁不住地要体睐、联想和感慨一番。从这一点来看,淳子的粉丝都是有质量的,他们不懒惰,不肤浅,懂得从一行字里,看出两行意思。 淳子笔下的上海女人都是很另类的,很多叫人看不懂的。淳子视野中的上海民国女子,就更加另类,更加叫人心疼,她们的心理历程大多触目惊心。因为她们优秀、美丽、有才气,也就有对手;更因为她们的坎坷、胆识和勇敢,也就更有故事。即便是大红大紫的电影明星和舞台宠儿,如胡蝶、秦怡、阮玲玉、陈云裳、张织云、袁雪芬、马樟花、黄宗英、上官云珠等,淳子也没有给多少令人眩晕、耀眼夺目的光环,而是深入她们的骨子里,看走下银幕或舞台的名角儿们,在褪去脂粉气的掩饰之后,在无法躲避的灾难和困惑面前的一切。至于那些海上名媛、大家之后,如李菊耦、张爱玲、孙用蕃、盛爱颐、吴靖、朱章绣等,她们在淳子笔下,更像是走出红楼梦的白发姐妹,在“忽喇喇似大厦倾”的年代,各自演绎出一部又一部鲜为人知的海派版的《大宅门》。
更加另类的其实是淳子自己。这些年,她竟大胆地关注着一个很不好整、并且并不怎么讨好的群体——卷入政治漩涡的妓女。听听都有些毛骨悚然,妓女已经够悲惨的了,还要加上政治色彩,无疑更加危险。事实证明,这个群体在任何时代都是危险分子。书中的含香老五、玲花老九,就是这样的人物。自然,现在淳子写出来的还是冰山之一角,是她们的故事的序篇,重头戏还在后头,因为重头戏的发掘本身也是非常艰巨而危险的。当我们享受着她的努力成果,深陷在她给的意境、故事、警句和觉醒中的时候,这中间的一切跋涉、考证、误解、困惑和苦恼,都由淳子一个人担当着。
这就是淳子最勇敢的地方,也是最值得佩服的地方,这种勇敢别人做不来。这其中或许有着她的家族遗传——淳子的父母都是当年潘汉年同志手下的白区工作者,一辈子浑身是胆雄赳赳。如今她那年迈的母亲送客出门,仍旧是当年地下党的老习惯——她先出门,警惕地左看右看后,才放客人出门。能够想象吗?钢铁竟是怎样炼成的!
写上海容易,写出上海的另类很难,像淳子这样写上海就更难。我提醒读者注意她的新作,必定不会令大家失望。
拉拉杂杂,权作序言。
二〇一三年六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