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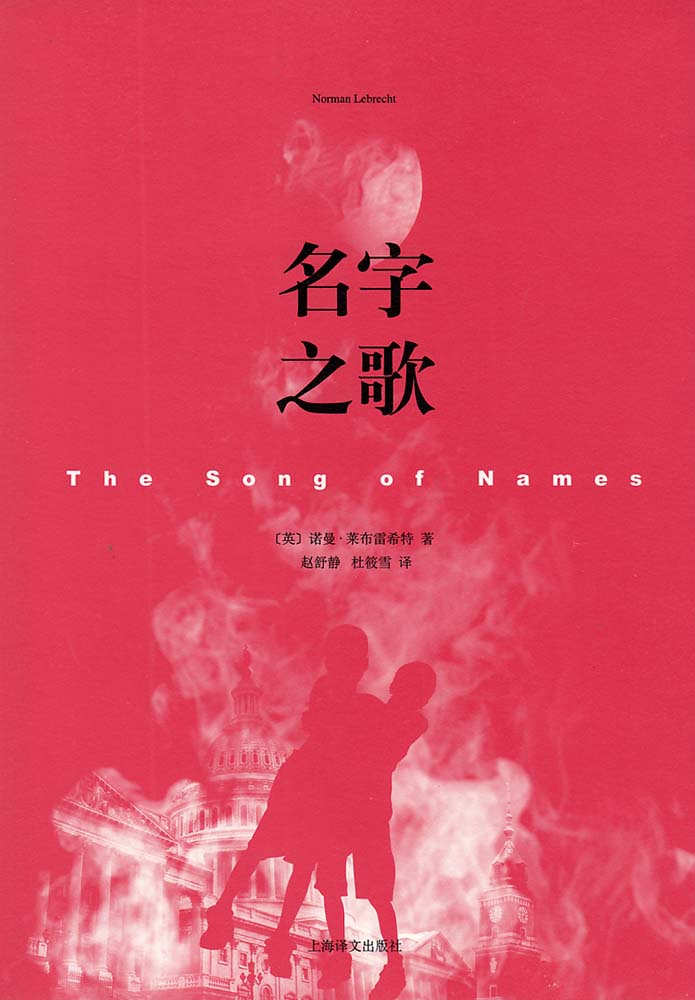 2002年《名字之歌》(The Song of Names)出版时,莱布雷希特本人已经54岁了。当这本书一举夺得当年英国的“惠特布莱德奖”时,英国媒体都感到惊讶,因为这本来是一个力推新人的小说奖,与他同台竞争的那些小说家都是30岁左右,而他秃顶,一把胡子,残余的头发已经变白,体形发胖,与人们的期待实在相去甚远。“有些艺术形式更适合年轻人,比如流行音乐或者戏剧。而小说这东西就和交响乐一样,适合沉思。年纪大有年纪大的优势,你的生活经验更丰富也更成熟,而且我想我写的时候才53岁。”他笑道,“其实我20多岁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想写小说,同时也知道我还没准备好。当我还在当记者的时候,经常说服我的编辑让我暂停工作几个星期,跑到世界的某个偏僻角落,待在那里写点东西。但在离开前,我又把我写的东西都撕掉,因为还不够好。” 2002年《名字之歌》(The Song of Names)出版时,莱布雷希特本人已经54岁了。当这本书一举夺得当年英国的“惠特布莱德奖”时,英国媒体都感到惊讶,因为这本来是一个力推新人的小说奖,与他同台竞争的那些小说家都是30岁左右,而他秃顶,一把胡子,残余的头发已经变白,体形发胖,与人们的期待实在相去甚远。“有些艺术形式更适合年轻人,比如流行音乐或者戏剧。而小说这东西就和交响乐一样,适合沉思。年纪大有年纪大的优势,你的生活经验更丰富也更成熟,而且我想我写的时候才53岁。”他笑道,“其实我20多岁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想写小说,同时也知道我还没准备好。当我还在当记者的时候,经常说服我的编辑让我暂停工作几个星期,跑到世界的某个偏僻角落,待在那里写点东西。但在离开前,我又把我写的东西都撕掉,因为还不够好。”
“这本小说探讨的更多的是一种哲学命题,艺术家和经纪人的对立,物质世界和精神生活的对立,而作为《谁杀死了古典音乐》等书的作者,莱布雷希特对于音乐行业生态的批判态度在这本小说里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杨燕迪评论道。与之相应,他认为,“书里的主人公形象显得有些生硬,似乎是根据某种理想概念在构造主人公性格,从而使其变成某种理念的代表”。
以色列作家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曾被莱布雷希特称为影响他最深的前辈小说家之一。《名字之歌》中,小提琴天才戴维多也颇具辛格笔下主人公的一些气质:与生俱来的天分,却又同时具有自毁的倾向,试图将自己沉浸在世俗世界的欢愉之中;性关系混乱,嗑药或者赌博,却无法摆脱罪孽感,最终寻向宗教救赎,完全舍弃了世俗生活。有人曾问过莱布雷希特,戴维多到底有没有形象原型?熟知古典音乐史的他坚决否认了这一猜想,甚至指出他自己特别小心地不要把戴维多塑造成任何一个人们已知的小提琴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小说讲的是音乐如何运作,没有围绕在音乐周边的人所贡献的想象力,音乐本身是不可能发挥作用的。”莱布雷希特说,“音乐家们其实是一群危险人物,需要有世俗的正常人小心地引导他们进入现实世界。从音乐产业的角度看,戴维多和马丁其实是同一个人,是一个整体的部分,缺乏任何一方都不会完整。”
不少评论家都注意到书里马丁·西蒙兹的父亲老西蒙兹这一人物的刻画,笔墨不多,却异常鲜明生动。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位职业经验丰富的音乐经纪公司老板教育儿子马丁如何与艺术家们打交道时那些堪称格言的台词——“永远不要相信音乐家言爱,永远不要相信经纪人谈钱”;“我们看起来越卑鄙,他们才越闪耀”;“若要在拯救人类和更衣室里有蓬松毛巾之间做个选择,他们总会选择毛巾”。
可以说,只有以莱布雷希特这样浸淫于古典音乐中几十年的阅历,才可能发表出这些洞见。而他对音乐家们的熟悉程度,几乎到了令音乐家本人都惊叹的程度。“《名字之歌》出版后几个月,我曾接到一位旧友的电话,来自一位非常著名的英国指挥家,圣马丁室内乐团的指挥内维尔·马里纳。”莱布雷希特回忆道,“他问我认不认识一位叫艾尔伯特·斯伯丁(Albert Spalding,1888~1953)的小提琴家,我说当然不认识,他在我出生前就已经停止登台了。他问我:‘你是如何知道他是怎么对他的学生说话的?小说里有一段他和戴维多的对话,一字不差的,他曾经对我说过。’我说:‘我不知道,我是凭与你们打交道的经验来猜想和创作的。’”
“名字之歌”这一短语来自莱布雷希特本人的发明,他将之称为小说的关键内核。“指的是一群犹太人纪念在大屠杀中丧生的同胞的生命,他们为了记住每一位死者,就把他们的名字编成一首歌吟唱出来,算是用来增进记忆的一个音乐对策。”莱布雷希特解释道。这个创意来自他真实的经历。有一次他参加一个犹太家庭的聚会,朋友80多岁的老父亲坐在桌边,哼唱着一支曲子。他询问这是什么旋律,老人回答是儿时从拉比那里学来的。“我一直很好奇,从前波兰各个犹太拉比是如何向他们的信徒传播新歌曲的,这些拉比们通常离群索居,住在郊区,远离尘嚣,而信徒通常住在城里,相隔一两百公里。传播的途径到底是什么?”莱布雷希特说,“原来传播途径之一就是这位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