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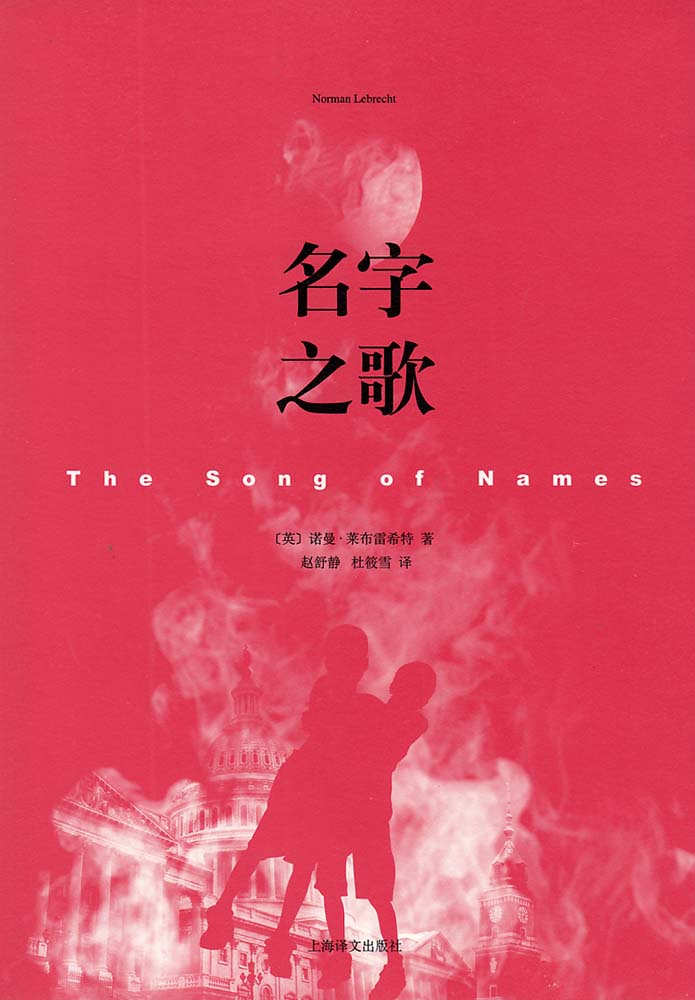 “……无人目睹有人从车里出来,警方称在不到零度的气温下,寻找到生还者的希望渺茫。”……他朝桥上站着的一群男人点了点头。他们戴着黑帽子,穿着黑大衣,左右摇晃着身体,伤心恸哭。这场面铭刻在我眼底,我的双耳和血液中的每个基因都把我拉向桥上的犹太人,我垂下头,为失踪之人的生死吟起诗篇:“我向群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听见他们的领袖哭喊着,大卫的每个字词都重读到支离破碎的地步。 “……无人目睹有人从车里出来,警方称在不到零度的气温下,寻找到生还者的希望渺茫。”……他朝桥上站着的一群男人点了点头。他们戴着黑帽子,穿着黑大衣,左右摇晃着身体,伤心恸哭。这场面铭刻在我眼底,我的双耳和血液中的每个基因都把我拉向桥上的犹太人,我垂下头,为失踪之人的生死吟起诗篇:“我向群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听见他们的领袖哭喊着,大卫的每个字词都重读到支离破碎的地步。
这是诺曼·莱布雷希特的小说《名字之歌》(Song of Names)中的一个情景。具有非凡才气的小提琴手戴维多在首演当天突然不知所终,给儿时好友莫特留下了无限的悬念和遗憾,几乎毁了他的生活。四十年后,一次偶然的机遇使莫特与戴维多再次相逢。戴维多已经换了一个身份,但仍然没有忘记拉琴,他说哪怕是一首婚礼颂歌,他也能拉出二十分钟的变奏,他的这种使时间停顿或飞逝的本领是只有帕格尼尼才掌握了的技能,在音乐厅里已经消失了近一个世纪。莫特准备重新把戴维多推上舞台大展才华,雄心勃勃地算计着让他补偿失去的岁月,尤其是报答莫特一家对他的养育之恩。但是,几天之后,戴维多却驱车坠入了距公路桥下六十英尺冰冷的河水中。
“‘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上主而来,’其他人回应道。他们拖长最后一个音节,不愿接受上帝对他们的祷告毫无回应的事实。”这样的情节惊心动魄,场景催人泪下,但是莫特突然想到了另一种可能性,收起了眼泪。他还暗自庆幸这一次他只是刚刚开始制定计划,不像四十年前,担任音乐经纪人的父亲竭力想要打造一个全新的克莱斯勒,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戴维多这颗即将升起的明星身上,最后却名誉扫地、经济损失惨重,争强好胜的母亲几乎精神失常,莫特自己则像失恋的人一样沉湎于往昔难以自拔,既时常牵挂戴维多的安危,又因为自己无故被抛弃而倍感尊严受挫。
莫特发现,当年吸引戴维多逃避舞台,放弃名扬天下机会的是“名字之歌”。从纳粹集中营幸存下来的犹太人确认死亡同胞的身份后,为了将他们的名字牢记在脑海里,在晚间祷告时吟诵这些名字,像唱一首复调歌曲,直到联系上死难同胞的亲人,按照犹太传统为亡灵举行追思。戴维多在波兰的家人几乎全都被纳粹送往死亡集中营,他得以幸免,是因为父亲带他来伦敦师从著名小提琴教师学艺,寄住在莫特家里。那是1939年,当时世界根本没有预料到希特勒会丧心病狂至何等程度。战争结束后,“可怕的真相来得断断续续”,人们在影院观看解放集中营的情景,所见纳粹的野蛮和暴行用言语无法形容,外面“生机勃勃的春季黄昏”似乎也充满讽刺意味。犹太人纷纷寻找留在纳粹后方的亲人,戴维多一家却始终没有音信。
亲人存亡未知,戴维多渐渐对音乐失去了兴趣,莫特父亲特地为他购置的1742年制作的瓜达尼尼小提琴也未能唤起他长久的热情。但是,他的音乐演奏天生有克莱斯勒之风,对巴赫等音乐大师的诠释超凡入圣。当他终于决定在音乐家的舞台上崭露头角时,莫特父亲巧妙地利用他的中间名伊莱(Eli)为他作宣传,因为伊莱听上去古雅别致,且能让人联想到万能的上帝,再配上他的姓氏Rapoport(形似rapport),似在告诉众人这位天才小提琴手是人神之间和谐交流的媒介,他能给“造物主怀着神圣的意图赐予我们的音乐”注入新的血液。然而,首演当天,他却不辞而别,还带走了那把价值不菲的瓜达尼尼小提琴。
莫特再见到戴维多时,他已经在极端正统犹太教派与世隔绝的生活中找到了宁静。这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他不再需要承受人们对天才的期待,而研习《托拉》的过程也堪比演绎巴赫的音乐,人们凭直觉和经验琢磨每节经文的内在意蕴,还能找到更多种诠释。戴维多出生在华沙的犹太人区,那里贫穷拥挤,却充满生活气息,儿童的天赋得到自由发展,这可能也是后来极端正统犹太社区生活吸引他的原因之一,他能在这里摆脱侥幸生存的负罪感和梦魇,而被纳粹杀害的三十九个家人的名字全都在他重建家庭的成员身上得到了复活。戴维多依然拉琴,那把瓜达尼尼小提琴在不明就里的人们眼里不值钱,但他轻轻触动琴弦,却能使一个窄小的空间变得像大教堂一样宽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