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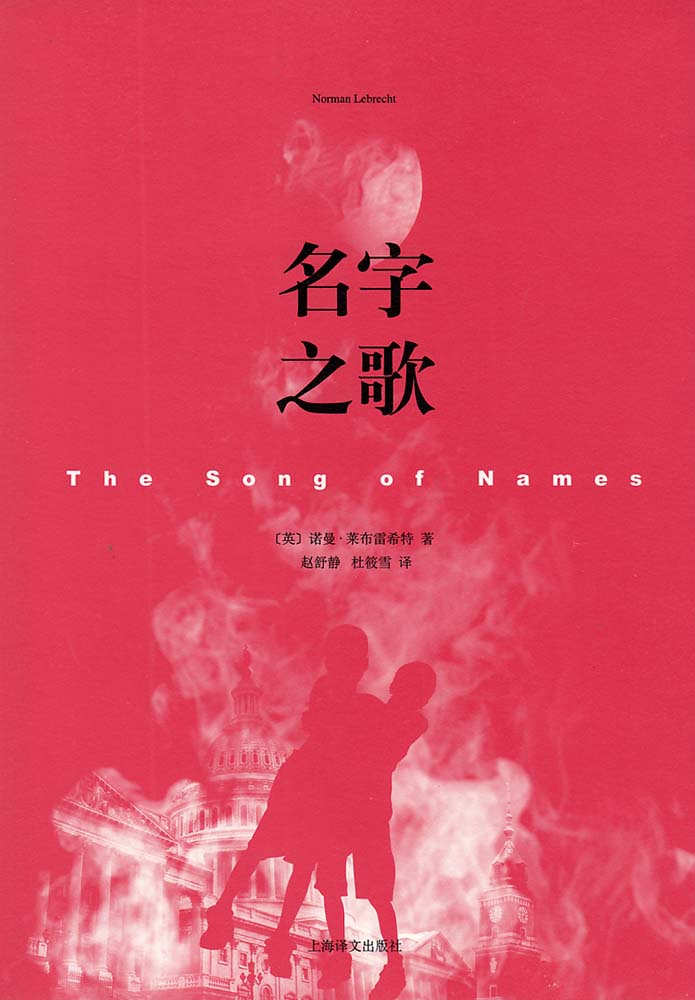 提起英国古典乐评家诺曼·莱布雷希特,人们马上会想起他的《谁杀了古典音乐》、《音乐逸事》、《永恒的日记》等著作。这位以观点犀利、文风泼辣而著称的乐评家,在中国拥有不少粉丝。不过,你也许不知道,莱布雷希特还是一位写小说的好手。他的小说处女作《名字之歌》一出手,就获得了2002年的英国“惠特布莱德奖”,其文学功力可见一斑。 提起英国古典乐评家诺曼·莱布雷希特,人们马上会想起他的《谁杀了古典音乐》、《音乐逸事》、《永恒的日记》等著作。这位以观点犀利、文风泼辣而著称的乐评家,在中国拥有不少粉丝。不过,你也许不知道,莱布雷希特还是一位写小说的好手。他的小说处女作《名字之歌》一出手,就获得了2002年的英国“惠特布莱德奖”,其文学功力可见一斑。
《名字之歌》的故事足够引人入胜:音乐公司的老板西蒙兹接待了一位从华沙流浪到英国的犹太小提琴神童戴维多,他出类拔萃的琴技让西蒙兹仿佛看见了“克莱斯勒第二”即将问世,便毫不犹豫地收留了他。从此,戴维多与西蒙兹的儿子马丁朝夕相处。马丁既是他的钢琴伴奏,又是他的同学和玩伴,两人形影不离。渐渐地,马丁习惯了自己老二的位置,就像安东尼之于恺撒,艾登之于丘吉尔,目标只有一个———有朝一日将戴维多推上国际音乐舞台的中心,迎接那辉煌的一刻。然而,就在马丁父亲精心筹划、众人期待已久的伦敦首演的前夕,戴维多神秘地失踪了,就此杳无音信。西蒙兹公司因而名声扫地,几乎破产,马丁父亲抑郁去世……时光流逝,四十年后,马丁前往一座小城担任音乐比赛的评委会主席。从参赛的小提琴手斯坦普的琴声中,他捕捉到了那似曾相识的律动。一番询问,马丁确信:斯坦普就是戴维多的学生。循着斯坦普提供的线索,马丁找到了戴维多的家,一对青少年时代的朋友终于重逢,不过,此时的戴维多已变成了一位犹太拉比。马丁提醒他“有债要还,有约要赴”,必须补开迟到了四十年的音乐会,然后跟随马丁前往世界各地巡回演出,以弥补西蒙兹家的损失。戴维多只好答应。但是,就在音乐会即将举行之际,戴维多出了车祸,连尸体也没有发现,只留下了那把价值三百万美元的瓜达尼尼小提琴,还有给马丁的一封信……
这部小说的情节一波三折,故事扣人心弦。戴维多两次离奇失踪,构成了小说的悬念,刺激着你一定要读下去,去解开这个疑团。不过,假如你把它当成悬疑小说来欣赏,那就是误读了。《名字之歌》的主题耐人寻味,它其实讲的是光鲜亮丽的古典乐坛背后音乐家真实的生活,以及在他们的音乐人生中所呈现出的复杂的人性。戴维多是个才华横溢的小提琴家,但在现实生活中他的形象并不单纯,战乱、家庭的不幸遭遇,给他的成长经历投下了浓重的阴影,他扭曲的个性其实在第一次失踪前就时有显露。纳粹空军轰炸伦敦之后,整座城市燃烧着熊熊火光,戴维多居然赞叹这“太美了”,将之比作斯特拉文斯基的芭蕾舞剧《火鸟》,让马丁不寒而栗;在大轰炸后的废墟中,马丁惊讶地发现,戴维多居然从一具残缺的尸体里找到钱包,抽出三大张白花花的钞票后,又若无其事地把钱包扔回废墟中; 至于与妓女调情,熟门熟路地带着马丁去污秽的赌博俱乐部,炫耀自己的赌技,则让马丁见识了他个性中更多的阴暗面。就像戴维多后来对马丁吐露的心声:“小提琴是能够展现演奏者一切的唯一乐器:他的优美,他阴暗的一面,统统展现……”另一方面,戴维多一直牵挂着滞留华沙的亲人的命运。在伦敦首演的前一天,他得知父母和姐妹都惨死在了纳粹的集中营里。刹那间,他感到整个世界都毁灭了,让他的双臂沉重无力,“若抬不起琴弓,我还怎么演奏?”于是,戴维多悄悄搬到了犹太人居住区,在同胞的关怀与犹太教古老严格的礼仪中,找到了心灵的归宿,也逃避了艺术与名利加在他身上的不能承受之重。而四十年后戴维多的第二次失踪,也由他自己一手导演。他无法面对马丁,面对马丁一家;生活的黑暗与磨难也让他不再相信艺术的神话,“我当然喜欢,可巴赫和贝多芬却无法治疗我的创伤”。戴维多于是用令人匪夷所思的方式选择了第二次失踪,也选择了逃避和放弃。
莱布雷希特将这个神奇故事的相当一部分置于二战的时代背景,为我们呈现了战时伦敦的音乐文化生活与人们的精神面貌。父亲领着马丁和戴维多去听夏季逍遥音乐会,指挥亨利·伍德爵士在演完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后愤愤地宣布,逍遥音乐会要停办了,因为英国广播公司准备遣散乐队;马丁和戴维多随西蒙兹去乔治·奥威尔家喝茶,奥威尔的直率和辛辣给马丁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战火纷飞的岁月,催生了英国许多知名作曲家,如沃恩·威廉斯、迈克尔·蒂皮特、本杰明·布里顿等人的一批优秀作品的诞生,成为英伦三岛不屈精神的象征。这些描述使小说闪耀出深沉的历史感。正是在这样一种富于英伦风情的时代氛围中,作家讲述了一个有关忠诚与背叛、崇高与卑劣、追求与迷失以及担当与逃避的故事,他一改写作乐评时毒舌般的尖锐,而是走起了温情路线,徐徐道来,使整部小说散发出感伤的气息,又不无思辨的色彩,进而让读者领悟到生活的复杂奇诡与人性的深不可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