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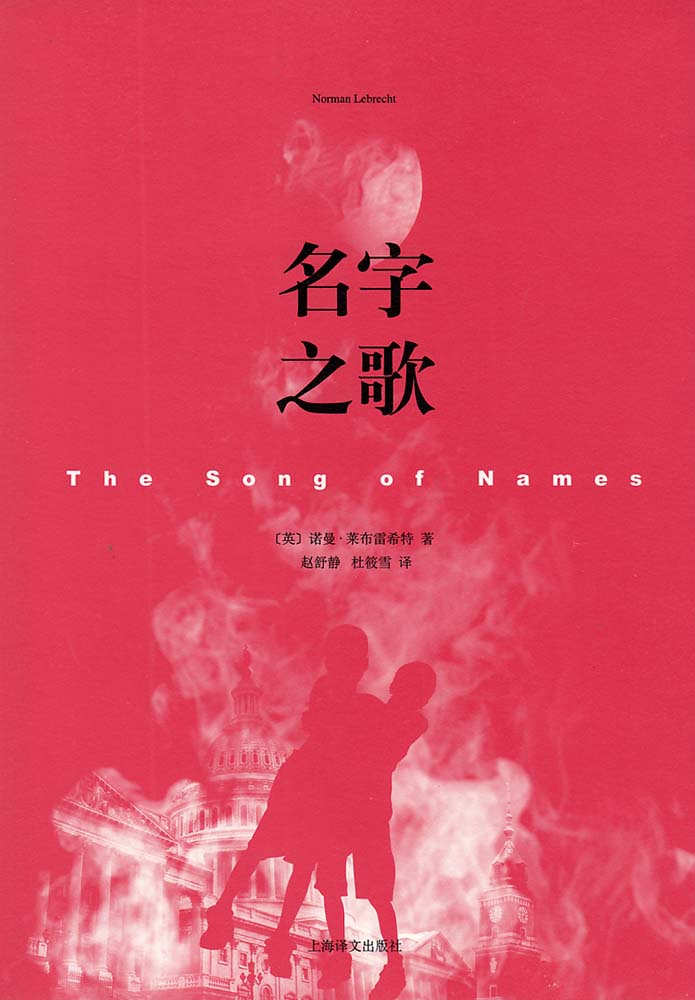 诺曼·莱布雷希特绝对算得上是个传奇人物。他年纪轻轻就当上高级制片人,觉得这工作“不够刺激”竟就摇身变为拥趸众多的乐评人:学院派满嘴阳春白雪范儿的技术术语,他偏要辟出一条下里巴人味儿的野路子,十年如一日,一门心思深挖着音乐大师背后的商业运作、艺术与金钱的权力关系,孜孜不倦发掘着音乐才子不为人知的八卦轶事、绯色新闻。无论是李斯特费尽心思的自我包装和推销,还是卡拉扬垄断音乐制作和门票价格的野心,不管是亨德尔暴怒之下甩了假发露了秃顶,还是阿图尔·鲁宾斯坦和安娜贝尔·怀特斯通相差六十岁的忘年“地下情”,通通都是莱大嘴的猎物,荤素不忌。 诺曼·莱布雷希特绝对算得上是个传奇人物。他年纪轻轻就当上高级制片人,觉得这工作“不够刺激”竟就摇身变为拥趸众多的乐评人:学院派满嘴阳春白雪范儿的技术术语,他偏要辟出一条下里巴人味儿的野路子,十年如一日,一门心思深挖着音乐大师背后的商业运作、艺术与金钱的权力关系,孜孜不倦发掘着音乐才子不为人知的八卦轶事、绯色新闻。无论是李斯特费尽心思的自我包装和推销,还是卡拉扬垄断音乐制作和门票价格的野心,不管是亨德尔暴怒之下甩了假发露了秃顶,还是阿图尔·鲁宾斯坦和安娜贝尔·怀特斯通相差六十岁的忘年“地下情”,通通都是莱大嘴的猎物,荤素不忌。
老莱伶牙俐齿,眼光犀利,文风老辣,不按常理出牌,严格说来虽是音乐界的圈外人,却一开口就有指点江山的气势。喜欢他的人,说他的文字另辟蹊径,把高高在上的古典音乐谱成了大众文学;膜拜他的人,说他的批评针砭时弊,把无人知晓的行业黑幕曝得妇孺皆知;当然,恨他的人巴不得马上送他去蹲牢房。《当音乐停止时》(在美国出版时书名被改成了火辣辣的《谁杀了古典音乐》)、《大师神话》和《大师、杰作与疯狂》是莱大嘴对古典音乐产业的“揭短爆料三部曲”,急功近利的音乐名流、唯利是图的唱片公司、僵化腐败的传统体制都被列为揭露对象,一时间他争议不断,树敌无数,还因为最后这本惹了官司上身。尽管老莱把这类作品都纳人“非小说”的行列,声称写的全是facts(事实),还凿凿地表示“所有听来的小道消息都会去查证,起码得有三种不同来源同时证明的消息才算可靠”,但从原告海曼先生的“15条驳斥”和出版商企鹅又是赔款又是道歉又是撤书的结局看,老莱的“非小说”中估计也没少掺道听途说、艺术夸张和二度创作。老莱骄傲而无畏地走在自己的野路子上,因揭露美国大都会歌剧院幕后交易而被封杀也罢,因“有违客观报道”而被《纽约时报》频频攻击也好,他只把对手的抓狂视为对自己的肯定。
老莱不服老,与时俱进地开微博,挂推特,写脸书,上电视,精力充沛地满世界跑,年逾五旬还精神抖擞地写下了处女小说《名字之歌》,圆了当小说家的夙愿。诗人是早慧的,小说家是晚成的——这后半句用在老莱身上再贴切不过,而他也从未让我们失望过:这部小说中,他竟一改煽动性的凌厉风格,走起了温隋路线。文字阴冷中露着温暖,像伦敦的天气,怀旧中透着伤感,如伦敦的街道。流淌在彼时彼此之间尚是朋友的轻松自然,以及心中又爱又恨、非爱非恨的暧昧情愫,像是为记忆中两人相处的画面蒙上了一层仿古色调的光晕,就连承载这些记忆的场所、背景和时代,竟也跟着温柔而美好起来。怀旧的旋律一流淌,又有谁的心不柔软?
我一度不喜文论和作者生平、精神分析云云搅和在一起,感觉好比评论鸡蛋的口感,非要铆劲儿钻研生蛋母鸡的家世背景和精神状态,生蛋时的情绪是否稳定、阵痛是否强烈。不过看到这套东西用在老莱的小说上偏偏就没有违和感,想来或是因为他的书里和书外、小说和非小说、虚构和现实打一开始就已经是舀不开的一锅粥。莫特在后院的椅子上自导自演的寂寞童年,两个犹太少年在英伦半岛的成长点滴,戴维多为寻找犹太身份的认同消失和漂泊N年,犹太人内心强韧却又有着触碰不得的脆弱,分明是一张张记录下老莱生平经历的书页;小提琴演奏家背后的推手,经纪公司的手腕,媒体的捕风捉影,分明是一面面映照出老莱生活阅历的镜子。
明星运作和小说创作看似书里书外八竿子打不着,在老莱这儿却是一脉相通:拥有迷人关键词的角色设定是成功的第一步。经过设定的音乐家个个都有炙热的艺术热情、潇洒的举止言谈,此时只要再凸显一两个迷人的关键词,马上就有画龙点睛之效,在媒体的助推下光芒万丈:莫扎特的关键词是“神童”,托斯卡尼尼是“过目不忘”,门德尔松是“描绘性浪漫主义”。仿佛缺了关键词的,就不能称为音乐大师——这个结论很怪异,但不失趣味。关键词以外的广袤空白留给了“秘闻”、“轶事”,越普通、琐碎、无聊就越能满足民众强烈的八卦心,想想看,高台上尽善尽美的神明,一回头竟是菜市场讨价还价的大叔,小失望之余又高兴地觉得和大师间的距离似乎拉近了那么一点点,不忘满足地评上一句:啧啧,也是个普通人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