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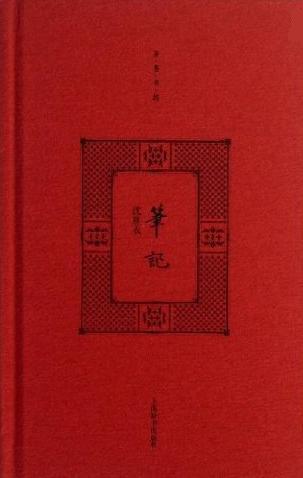 沈胜衣的《笔记》系“开卷书坊”第二辑之一,“开卷书坊”是以弘扬书香文韵为宗旨、图文并茂的书文化随笔丛书,本辑12册。丛书作者有来新夏、姜德明、扬之水、许宏泉、沈胜衣、桑农、范笑我、彭国梁、韦泱、子聪等。丛书开本精巧,由多次荣获“中国最美的书”的设计师朱赢椿任书籍整体设计工作,别具一格。 沈胜衣的《笔记》系“开卷书坊”第二辑之一,“开卷书坊”是以弘扬书香文韵为宗旨、图文并茂的书文化随笔丛书,本辑12册。丛书作者有来新夏、姜德明、扬之水、许宏泉、沈胜衣、桑农、范笑我、彭国梁、韦泱、子聪等。丛书开本精巧,由多次荣获“中国最美的书”的设计师朱赢椿任书籍整体设计工作,别具一格。
巨星都不能掀起轰动的园子
当年读了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后,去北京时便专门拜访了这座公园。
园不大,也没什么名胜,它更接近于合家休憩的园子,而不是那些招徕游客的“旅游热点”。林子里,疏碎的阳光与清风中,有一个坐轮椅的男人正在读书,过去闲聊两句,那人说,史铁生开会去了,这几天没来。这位因行动不便而更多地转向思想,从而提前成为智者的作家,确实在这里留下了气息。
然后看见一个冷峻的男人在一边摆造型拍照。细一看,是崔健。等他拍完照,我和另两个青年过去请他签个名,说几句话,然后各自散去,和声细气,不远处散步的老人们、嬉戏的孩子们完全没有受到打扰。
如果当时仍红透半边天的崔健是出现在其他地方,那该出现怎样的惊呼、争逐、狂热、喧闹?然而在这座随随便便、平平常常的园子里没有这些。这么想便觉出地坛素朴的伟大,一座连巨星都不能掀起轰动的园子。
黄永玉先生的 《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里有一篇谈公园的,大意是,公园原本都是古时帝王将相的花园,留下来便成为老百姓的了。董桥先生则说过,在经济、科技的大堂后面,该经营让台静农先生抽烟、喝酒、写字、著述、聊天的后花园。
帝王将相造花园,本意就是为了办事之余的清静。我想,以造物之伟大,是该留下这样一些单纯的后花园的,让老百姓走走,散散心,让智者坐坐,想想事,让呐喊的明星在这儿也不摇不滚,安安静静。
一九九六年一月
现代爱情故事
卡夫卡写过一个小故事。用时下语言来译,是这样的:他碰见一个漂亮姑娘,于是过去搭讪:“靓女,跟我走吧,好吗?”靓女不屑一顾:“哼,你又不是有名有利的大亨,又不是像美国佬那样魁梧迷人的男子汉,也不像个出洋掘金、有见识的人,我这样漂亮的姑娘,干吗要跟你?”
他也不甘心:“嘿,你别忘了,你本身也好不了多少,既没有汽车带着你兜风,身边也没有大款陪着。况且小姐你衣靓人美,你的微笑又那么迷人……”又打又捧,泡妞的功夫可谓到家,然而漂亮姑娘会有什么反应呢?
“是呀,我们讲的都不错,但就是为了避免我们不可挽回地意识到各自的缺陷,我们分道扬镳,各自回家,难道不更好吗?”靓女如是答。
这个叫“碰钉子”的故事在我们身边每天都发生(所以杰出的作家总是能跨越时空,捏住人类的本质的)。那姑娘可能永远都找不到如意郎君,但不能忍受一份永远在提醒双方低人一等的爱:我没能耐傍到大款,只好跟了你;我发不了达,只好娶了你——真的,与其这样,还不如“分道扬镳,各自回家”,各自孤独。那姑娘是对的。
卡夫卡一生婚姻无着。这个大胆泡妞的故事多半是虚构的,他不过是要告诉我们:勇气、欣赏……这些传统的爱情因素统统要碰钉子,在爱情已跟现实混为一谈的时代。
或许正因此,孤独才有了积极意义:它至少保存了可能性、希望和自信。又或者说:这些只有在孤独中才能被保存。
戒诗者说
梁实秋早岁以诗歌、小说起步,后弃之转向散文、翻译并以此成名。在《诗人》一文中他说:“入世稍深……散文从门口进来,诗从窗口出去了。”青春期过,入世稍深,是诗情泯灭的重要原因。当然还有其他因素,使诗人们自动搁笔(或搁笔一段长时间),如法国的梵乐希,台湾的痖弦、席慕蓉,等等。
时势也在施加影响:在旧日风暴浩劫的背景下,有流沙河、公刘、邵燕祥变成杂文家;在今日世情浮躁的背景下,有韩东等变成小说家。时代制造了更切身的现实、更多变的口味和选择、更繁杂的消遣物和文学体裁,促成了诗与诗人们的集体退场,另寻新路。大陆诗坛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盛衰转换之快,令人恍如隔世。
时代也在弃诗了。可是,台湾的夏宇诉说情愿做些生活琐事也不愿写诗,“诗显得太奢侈了/而且/有点无聊”——她却是在一首诗中(《诗人节》)写出这些的;王蒙在接受蒙代罗文学奖讲话中也为诗在现实社会的尴尬而感叹。但接着又说:“可怜的诗。在我们与诗相互忘却之前,为什么不再看她一眼呢?”这都是既洞见诗的命运又恋恋不舍的表现,这意思已够难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