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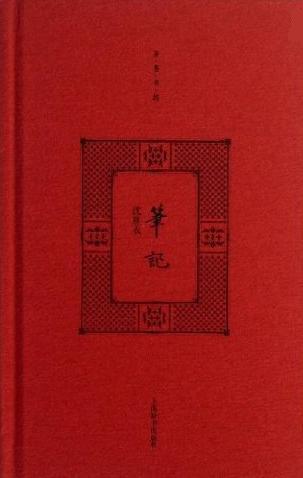 现在这本《笔记》,就尽量不选那些过于伤感忧郁的低回之作。但,因为各辑主题的需要,仍不可避免有部分要收录进来,既无法彻底割裂,也不应完全抹杀,那就作为旧我的一点点珍重纪念吧。然则,书中前后跨越二十年的新旧之作,也可视为二十年间的零碎心迹,记录了自己曾在何时有过怎样的心态——却并不代表当下。 现在这本《笔记》,就尽量不选那些过于伤感忧郁的低回之作。但,因为各辑主题的需要,仍不可避免有部分要收录进来,既无法彻底割裂,也不应完全抹杀,那就作为旧我的一点点珍重纪念吧。然则,书中前后跨越二十年的新旧之作,也可视为二十年间的零碎心迹,记录了自己曾在何时有过怎样的心态——却并不代表当下。
感谢宁文兄和他的“开卷”,是那样的宁和文事、开放书卷,才有了我这本广义的读书笔记。
我曾经跟朋友讨论过“广书话”的概念。盖因近年的书话写作与出版颇为繁盛,令人欣悦的同时却又渐感程式化,尤其是题材集中于现代文学、文史古籍和中西藏书等方面,雅则雅矣,却大都在同一格调中打转;而我,希望能看到题材与写法更宽广、更有生活气息的谈书文字。
很高兴,宁文兄的邀约信函里特别提到,“开卷书坊”是一套“开放性丛书”,“内容并无具体或统一的要求,关键在气息。”立意正与我的想法相契,遂编成这样一部散漫的书稿:
辑一“斯人斯书”,是向谷林先生致意。对于这位尊敬的老人,我2005年出版的《满堂花醉》收录过若干记写,这里是后来的几篇书评和怀念文章。(后面的植物两辑也有多篇涉及老人。)
辑二“一瓢饮”,我第一次专栏写作的选辑,一些闲阅杂览、随感漫思的小品札记。
——以上两辑,尚勉强能与传统意义的书话沾点边,以下就是非主流的另类书话了。
辑三“书边影迹”,谈与电影有关的书,更谈与书有关的电影,主体是文学改编电影的话题。
辑四“书外余音”,谈与流行音乐有关的书,更谈与文学作品有关的流行音乐,特别是写了几位身为作家的港台词人、歌手。
辑五“花名册”,专门记述以植物为书名、却又不是植物专著的文史书籍,是植物与文学的交汇处,牵藤带瓜地闲聊寄兴的读书随笔。
辑六“草木书情”,则基本是关于植物专著了。我近年颇有兴致于“植物书话”写作,包括与书(文史)有关的植物,和与植物有关的书两大类,考虑到“开卷书坊”的基调,这里选收后一类篇章,即主要不是以植物、而是以植物图书为对象,作些介绍评点,谈些购读琐思。以书话风格来写植物的前一类,只存《隔帘抛与沈郎书》以见一斑。至于最后的新作《从书之书到树之书》,恰好反映了我不同方面的兴趣、涵盖了本书的编排脉络,宜于作为殿后压轴。
——音乐电影之声色,花草树木之植物,是贴近我们日常生活的,有实实在在的生命质地,因此,我愿意将它们与超脱现实的读书联系起来,庶几使读书与人生不即不离。
需要说明的是,各文所谈话题,一般只限于落笔时的所见所闻。这个新春三月编选时,对一些旧作的文字乃至篇章本身作了修订(很多文章比在报刊发表时略有增删),但涉及的相关资料未全部补充,比如“花名册”系列,以及“戏言之书”、“知音之书”等,写成后这几年又买了不少同类书,就没有反映出来。
资料如此,文章的心情亦然,都只有写作当时的意义。以前曾受邀编过两次书话散文类的书稿,均告夭折,这次回头重看,不禁庆幸当时没能出成书:从前的文章,写了太多幽衷心事、纷披故事、伤怀往事,浓浓浸透情思,深深自陷怅惘,细碎纠缠沉吟——让我第一次“悔少作”。现在这本《笔记》,就尽量不选那些过于伤感忧郁的低回之作。但,因为各辑主题的需要,仍不可避免有部分要收录进来,既无法彻底割裂,也不应完全抹杀,那就作为旧我的一点点珍重纪念吧。然则,书中前后跨越二十年的新旧之作,也可视为二十年间的零碎心迹,记录了自己曾在何时有过怎样的心态——却并不代表当下。
……
生活的美好,是可遇不可求的上天恩赐,有幸得之,当感激珍惜妙缘。就像这个春天,尽管寒暖不定,有明悦阳光也有阴郁雨雾,可是,它始终还是可爱的春天。同样,读书也应该是美好的。我这集子中有一篇《读书可以这样沉重》,但我愿意用这个自序的题目纠正一下自己:读书也可以这样声色花木,就像生活可以如此丰盛散逸。
那些与生活相关的书,那些与书相关的人,从巴乌斯托夫斯基到林文月……谢谢你们。(因版面篇幅所限,文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