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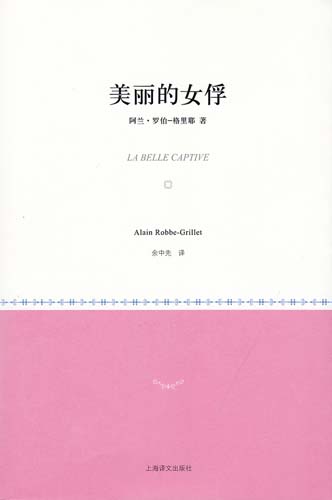 看纸质书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我们的地铁中少有捧书阅读的现象,在感叹的同时,我们是否想过,设计一种符合阅读习惯、手感超好的纸质书,让阅读本身变得更舒服、更轻松? 看纸质书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我们的地铁中少有捧书阅读的现象,在感叹的同时,我们是否想过,设计一种符合阅读习惯、手感超好的纸质书,让阅读本身变得更舒服、更轻松?
体育场路晓风书屋,进门左开间有一个书架。
如果只是一眼扫过,大概不会发现其中的特别:书架的中间三行,码放着一系列“小一码”的最新出版的书。与通常不同,它们不是单纯按照内容码放的,这些书里,涉及散文、小说、诗歌、哲学……之所以被集中到此,原因是它们的个头——如果在它们边上放一本主流开本的书,“小一码”便一目了然——3/4的体积,3/4-1/2的重量。
这让人联想起日本书店的“文库本”书架。
在日本,专门为小一码的文库本设立的书架非常普遍,家具店里,甚至有专门为文库本设计的书籍隔板。“文库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27年,日本的岩波书店为了对抗市场上豪华昂贵的经典巨著,推动文化传播,推出了一系列小巧、价格便宜的文库本。岩波书店的理想完美地达成了——文库本成为日本图书出版业的重要势力,日本人在地铁电车上阅读的习惯从明治维新时期一直保持至今,与文库本有莫大关系。
与此同时,在日本的地铁中,Kindle电子书难得一见。
与那三行“小一码”书对照的,是晓风书屋中的占据主导地位的大开本书。
店主朱钰芳回忆上世纪九十年代她刚入行时,“书架远不是现在的高度。但近十年,越来越多的大开本出现,就只能定制新的书架。”
大开本的席卷,背后必然各种因素交杂,比如更大的利润空间、码放时的抢眼程度,以及购书者的消费心理。情形的演变程度,甚至到了让人啼笑皆非的程度:精致厚实的大开本,翻开,留白是内容的一倍乃至几倍。
但是,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多“与国际接轨”的大书吗?
努力“消失”的Kindle
不得不提到Kindle。
这一全球第一大网络书店、美国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亚马逊的王牌阅读器,在过去的几年里,给传统的纸质书市场带来了极大的恐慌,并且势力还在蔓延。按照Kindle近年的表现——2010年,亚马逊美国的电子书销售超越纸质书销售;2012年,亚马逊英国也宣布,英国人购买的Kindle电子书首次超过纸质书——马上将在中国上市的Kindle将会作何表现,让人遐想。
Kindle在短短六七年里异军突起,全球网络化是重要的生态背景,但其强悍同样建立在,除了大容量、越来越轻巧、易于携带的体积,还有它不断“接近纸质书”的阅读体验。
Amazon亚马逊最大的产品经理贝索斯这样描述Kindle:“它从一开始就是一本书”,而它的最终目标则是“从你的手中消失”。这一“消失”,指的就是让Kindle使用者们忘记自己盯着的只是一块N英寸屏幕。
当“纸质书拥有纸所不能代替的质感”与“纸书的重量和有限容量”之间的争执多年后,Kindle在“消失”的路上飞奔,2013年还将继续扩张它的研发团队,而纸质书的设计,似乎始终停留在对外观的追求上。
从某种意义上说,纸质书的设计,与Kindle并无二致,同样是内容的载体。因此,我们不禁想,纸质书是否也能在纸张质感的基础上,让阅读变得更舒适、更愉悦、更不增加阅读者的负担,或者换一个词:更人性?
这一本书的阅读体验
并非没有趋向完美的范例。
让我们抛开书的内容,直接来看书的设计本身——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初出版的《我不是一本型录》可以用来作为标本。
书比正常的32开本小两个尺码,11.5×16.6,差不多是手掌的长宽度——一手就能掌握,但有没有窄小到逼仄的程度。事实上,这种开本,在中国的古籍中并不少见。
书的封面是棉麻的柔韧质地——此后,我们将看到它的特别所在。
拿起书,它的重量传递到你手中,只有同类书的3/4-1/2。
把书脊放在手掌中,打开,浅黄色的内页光泽柔和,因此书的字体虽然不大,但依旧让眼睛愉悦,另一个不累眼睛的原因是书的行间距,疏朗程度远离了傻大的字体带来的压迫感,却又没有不知所谓的大片留白。这一设计另一合理之处在于,开本尽管变小,书的内容量依旧得到保证:330页中,包括了近80页的图片和说明,依旧能容纳20万字。
翻页。第1页、第101页或者第301页,内页都温顺地躺倒,另一只手基本只需要翻页,而不用费心摁住不断企图合拢的书页。
合拢书,把它放进随身的包里,封面的特别所在显现出来:尽管是平装本,它却拥有着精装的优点:不会卷角,无论是内页还是封面;与此同时,又避免了精装本对承重能力的考验。
设计在这里,不是为了张扬设计本身或者吸引消费者的眼球,而是为了愉悦的阅读体验。
遗憾的是,这一类型的书寥寥无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