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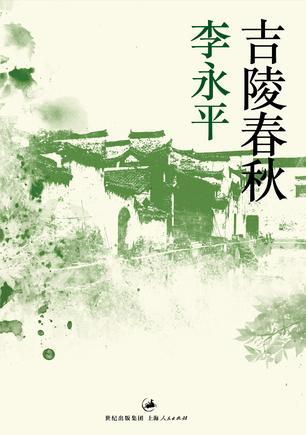 1976年秋天,来自南洋的“浪子”李永平,结束了在台湾大学的游学生涯,告别栖身9年的宝岛,再一次动身上路。这回一路漂流到新大陆,机缘凑巧落脚于美国东北的奥伯尼市,看到了生平第一场雪。 1976年秋天,来自南洋的“浪子”李永平,结束了在台湾大学的游学生涯,告别栖身9年的宝岛,再一次动身上路。这回一路漂流到新大陆,机缘凑巧落脚于美国东北的奥伯尼市,看到了生平第一场雪。
秋末的一个傍晚,李永平从就读的州立大学文学院走出来,整座城市笼罩在漫天飞絮中。他一路走,不知怎的一路回忆起,孩提时代发生在赤道丛林中的往事,那个在家乡小镇上“一头花发,弓着腰,驮着红包袱” 踽踽独行的孤单老妇人。因为这个记忆的强烈浮现和牵引,李永平开始着手写作“吉陵”系列——这就是后来的《吉陵春秋》。
该小说成书于上世纪80年代,2013年由世纪文景引进首次在大陆出版。2012年,李永平借他的《大河尽头》“回归”祖国,《吉陵春秋》是李永平被引进大陆的第二部作品。对李永平而言,《吉陵春秋》有着特别的意义。在80年代,他就以《吉陵春秋》一鸣惊人,博得王德威、龙应台、齐邦媛、刘绍铭、余光中、颜元叔等人的赞誉,并凭借这部作品入选了“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
《吉陵春秋》写的是不知神州何处的一个小镇——吉陵,镇上有一条烟花巷唤作万福巷。娼寮聚集中却有一家棺材铺子,女主人长笙素颜白衣,如污泥中的白莲,却不知那样清纯的美会变成一种诅咒。六月十九迎神夜,全镇人在巷口看迎神,泼皮孙四房起歹意乘机作恶,长笙被辱自尽,丈夫刘老实发狂杀了孙四房的相好和老婆,锒铛入狱。后报载刘老实越狱,吉陵镇上便谣传他要回来复仇。长笙被辱当日谁人没有罪?风声鹤唳,人人疑神疑鬼,说是长笙的冤魂白昼作祟,复仇者坐在苦楝树下等人……全书以“十二瓣观音莲”的方式,用十二个互相联系的篇章将这个中心场景补全和升华,将读者的心一直提着到最后都不得解。
或许因为李永平颠沛流离的经历,他的作品中总是扑面而来一种“陌生”的气息。1947 年,李永平生于英属婆罗洲沙捞越邦古晋市,马来西亚独立后,又从大英帝国的子民变成了马来西亚公民,但却愤恨这个“政客们炮制出来的国家”。为了离他真正的祖国中国更近,他选择到台湾读大学,此后除了在美国完成硕士和博士学位的 6 年,他再未离开台湾。
对话李永平:文学是结缘的最好方式
1 正在努力完成“大书”
深圳晚报:老师最近身体好吗?不知平日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手头还在创作新作品吗?
李永平:我做了心脏手术后,如今还在复元中,比起开刀前,身体情况好多了。我已从台湾东华大学退休,目前住在台北附近的淡水镇,平日闲来无事,又拿起笔来写新的长篇小说。这回,我把我的小缪斯——台北姑娘朱鸰——丢进婆罗洲的丛林,让她担任女主角兼叙事者,从事一趟奇幻的冒险旅程,书名就叫《朱鸰书》。因为生活规律,每天定时写作,这部作品进行得很顺利,现在已经完成了三分之一,再过两年应可出版。
深圳晚报:齐邦媛老师说:“李永平是真正读书甚多的学术中人,他近年中译西方文学作品亦很有成果。以他的学识、才情,和已可自信的写‘大’书经验,该是悠然走出雨林记忆和台北黯夜的时候了。”对这个建议,您怎么看,会写一部“大”书吗?
李永平:这是齐邦媛老师在《雨雪霏霏》(2002年)序文中对我这个学生的期勉。我正在努力呢!目前正在写的《朱鸰书》是《大河尽头》的后传,而《雨雪霏霏》则是前传。这三部小说构成一个三部曲,把我的婆罗洲经验做一个总结,书名也许就叫《大河三部曲》吧(河流是连结三本书的一条脐带,也是中心象征)。希望这个作品,至少在字数上(总共80万字),能够符合齐老师对“大书”的要求。
借用佛家的“三境界”来说,《吉陵春秋》可说是第一阶段——见山是山——的作品:看到的世界单纯而真实。写完这部小说后,我决定当个专业作家,不惜辞去大学教职,蛰居台湾中部山中,专心写作,花4年的工夫完成一部50万字的小说《海东青》(1992年出版)。但是,太过沉溺于文字技巧,竟写出了一本很少人看得懂的“天书”。这应该算是第二境界——见山不是山——的作品吧。
痛定思痛,返璞归真。我用比较朴实的文字风格和平易近人的表现方式,展开第三阶段的写作生涯——见山又是山。当然,经过40年的颠沛流离的人生历练,思想和世界观,都比《吉陵春秋》时代成熟多了。这需要读者自己的发掘和体会。
2 年轻马华作家乡愁渐淡
深圳晚报:大陆读者对马华文学渐渐熟悉,但发现书写有不同。您的书中仍有很多对祖国的眷恋,对华人颠沛流离历史的书写;而像黎紫书这样的年轻马华作家,更注重对自己所处当下的书写,并没有太多乡愁的诉求。可否介绍一下马华作家这个群体?
李永平:离散与乡愁、迷惘和寻找,一直都是马华文学常见的主题,只是我的表现特别深。马华年轻一代的作家,如黎紫书、钟怡雯、陈大为、龚万辉等,已完全认同“马来西亚”这个国家,所以在他们的作品中,离散和乡愁的色彩渐渐淡去。他们的理想和追求,与其他族裔的马来西亚作家并无不同。我祝福他们,希望他们能在南洋的土地找到“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