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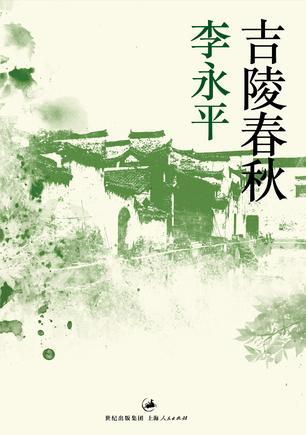 最近,《吉陵春秋》在内地出版。这部长篇小说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作者为现居宝岛台湾的马华作家李永平。1999年《亚洲周刊》邀海内外14位评委甄选的二十世纪全球华人中文小说100强中,名列第40名的《吉陵春秋》可谓最晚进入内地读者视线的遗珠。 最近,《吉陵春秋》在内地出版。这部长篇小说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作者为现居宝岛台湾的马华作家李永平。1999年《亚洲周刊》邀海内外14位评委甄选的二十世纪全球华人中文小说100强中,名列第40名的《吉陵春秋》可谓最晚进入内地读者视线的遗珠。
《吉陵春秋》的时空坐标均不明确,以烟花巷中的棺材铺为背景,以“十二瓣观音莲”的方式,用12个互相联系的篇章描绘了一个关于恶与恶之惩戒的“传说”。
《吉陵春秋》的底色是中国小镇形象还是南洋景观?是江南风物还是热带的古晋?李永平其实更强调的是一种具有典型特征的非个性空间,里面实践了四不像哲学。
长期以来,对于《吉陵春秋》意境和关涉主题的书写指涉争论不休。或者是中国小镇形象,或者是南洋景观,或者是江南风物,或者是热带的古晋等,不一而足。余光中在《吉陵春秋》序言《十二瓣的观音莲》中指出,“从虚构的立场说来,这本小说只宜发生在中国大陆。”齐邦媛教授则说,“李永平创作《吉陵春秋》时应未去过大陆,他对中国的想像纯然是文化性的。也许尚有侨居地的影子。”较早论及李永平《吉陵春秋》的曹淑娟却指出其中世界的混杂特征和神话色彩,认为“作者综合了他得自生活与学识的中国经验,营构了一个可以南、可以北的中国人生存空间。它的模糊暧昧,正可以舍离明确地点所必然连结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制度,成就一个带着神话色彩的世界,或许它类似于西方文学中的一些虚构的城乡”。
在我看来,李永平的吉陵书写毋宁更是一种本土的另类突破与超越——其独特的本土往往是旅行的、游移的,为此,其吉陵图像也相应地表现出一种混杂的、模糊的特征。
李永平的吉陵蒙上了一层朦胧色彩和有意模糊化的环绕。一方面,它其中运行了相对清晰大的地域、文化、社会背景;另一方面,这种混杂图像却有时有其互相抵牾之处,值得反思。具体说来,不难看出,《吉陵春秋》中的中国图像清晰可辨,哪怕是历史背景。军阀割据的余绪、铁路通行、外国宗教传入、南货(红椒)北销等等显然打上了中国的烙印。但同时,小说中的中国图像却又是朦胧的、不定的,你根本无法确定其具体区域特色和背后的省市文化底蕴。某种层面上讲,这正体现了作者对历史中国的消解。“南洋”色彩尽管并未如早期的书写那样或者标签化的蕉风椰雨那样醒目,但间或的对话习惯也点缀其中(“惊吓到了”,常见的说法是“吓着了”)。更进一步,稍微有点南洋体验和文本经验的人便不难发现,小说中有关天热的书写相当有特色,不仅分量极重(小说中的其他三季恍若缺席),而且风格独具:暴烈、阴暗、浓郁等。
耐人寻味的是,李永平其实更强调的是一种具有典型特征的非个性空间,里面实践了四不像哲学,其非中国、非南洋,又中国、又南洋的中性姿态也可以进一步得到论证。在小说中常常出现用作背景的(苦)楝子树其实也是“华北及南方各地”适宜种植的树种,显然作者在有意淡化或借此掩饰具体地域的色彩。
如果从语言角度进行考察,我们也不难从其表面的自相矛盾中体味“四不像”的哲学意味。在李永平刻意纯化的语言操作中,如果仔细检查,其中还有一些蛛丝马迹值得细究。“猪哥”(“这一群热铁皮上跳窜的小猪哥!”)作公猪、种猪解时,在闽、粤、客语中皆有所见;作“淫棍、色魔”解时,则见于客、闽话中;而“猪公”(“家里那口猪公也杀了”)则是普通话中少用的词汇,经查,发现它在晋语、福建官话、吴语、湘语、客话、粤语、闽语中皆有出现。我们如果根据这两个词语的交集,我们可以发现,小说极可能发生在广东或福建。
《吉陵春秋》营造的空间是典型化的“恶托邦”世界。“恶托邦”中群体的冷漠、集体无意识和帮闲从很大程度上讲深刻地延续了鲁迅笔下对国民劣根性的有力批判。
实际上,《吉陵春秋》营造的空间是典型化的“恶托邦”世界。《吉陵春秋》题目就显出别样的反讽:以春秋笔法写罪恶昭彰的“吉”陵,其实应该叫做《凶陵梦魇》的。“恶托邦”表现在小说中则有其相当繁复的表征,李永平似乎摆出一幅“恶不惊人死不休”的架势。但如果从“恶”的内外角度考量,我们大致可分为恶之本与无药可救两个层面。
表面上看,“恶托邦”吉陵表现出礼崩乐坏的零乱与失序,而实际上,“恶托邦”乱中有序,如果深入其中,则非理性的恶的主线昭然若揭。同时,如果从人的角度考察,无论是个体的沉沦,还是集体的冷漠与帮闲都形构了“恶托邦”互相连缀又有所区别的丰富层面。吉陵说到底是一个罪恶、腐朽、堕落的世界,也是一个人吃人、世态炎凉的冷漠社会。其堕落的重要表征就是对传统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等的漠视与破坏。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恶托邦”社会秩序的失序,致命的是,取而代之的是它本身的恶主线。
对主体意识和个性的弘扬到了“恶托邦”吉陵这里就慢慢变成了麻木、冷漠,甚至是帮闲与自奴化。不仅仅是男人对弱势的女人的种种欺压与凌辱,就连女性自己也往往缺乏必要的怜悯和同情心,甚至反过来成为谋杀同类的帮凶,甚至主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