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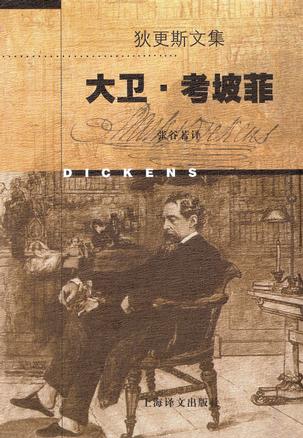 2月7日,于英国文学的爱读者来言,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二百年前的这一天,查尔斯·狄更斯在英格兰南部朴次茅斯诞生。在同时代作家安东尼·特罗洛普眼里,以15部小说赢得无数读者的狄更斯,“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受大众欢迎的小说家。也许他也是所有时代最受大众欢迎的英国小说家”。莫洛亚也记录了时代的见证:狄更斯1870年逝世时,消息传遍了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澳洲的每一个有儿童的人家;据说有一个小孩子曾经问道:“狄更斯先生死了吗,那么圣诞老人是不是也要死掉呢?” 2月7日,于英国文学的爱读者来言,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二百年前的这一天,查尔斯·狄更斯在英格兰南部朴次茅斯诞生。在同时代作家安东尼·特罗洛普眼里,以15部小说赢得无数读者的狄更斯,“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受大众欢迎的小说家。也许他也是所有时代最受大众欢迎的英国小说家”。莫洛亚也记录了时代的见证:狄更斯1870年逝世时,消息传遍了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澳洲的每一个有儿童的人家;据说有一个小孩子曾经问道:“狄更斯先生死了吗,那么圣诞老人是不是也要死掉呢?”
狄更斯的名声,如同莫洛亚所说,“至今依然差不多一点也没有动摇”;他在英国文学中的地位,“仅次于莎士比亚”(《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五卷)。在过去一个世纪里,他也是在中国影响最大的英国小说家。他在中国的历程,始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商务印书馆首次出版林纾和魏易联袂翻译的狄更斯小说。两年里,林纾翻译了狄更斯5部长篇小说——《滑稽外史》(《尼古拉斯·尼克尔贝》)《孝女耐儿传》(《老古玩店》)《块肉余生述》(《大卫·科波菲尔》)《贼史》(《奥立弗·退斯特》)和《冰雪姻缘》(《董贝父子》)。翻译“西士文字”四十年的林纾,对狄更斯评价最高。他说,“其间有高厉者,清虚者,绵婉者,雄伟者,悲梗者,淫冶者;要皆归本于性情之正,彰瘅之严,此万世之公理,中外不能僭越。而独未若却而司·迭更司文字之奇特”;而且还把狄更斯的叙事,同《史记》笔法相比拟:“余尝谓古文中序事,惟序家常平淡之事为最难著笔……今迭更司则专意为家常之言,而又专写下等社会家常之事,用意著笔为尤难。”而他在《块肉余生述》译序中,更表明了他翻译狄更斯的深意所在:“使吾中国人观之,但实力加以教育,则社会亦足改良,不必心醉西风,谓欧人尽胜于亚,似皆生知良能之彦,则鄙人之译是书,为不负矣。”那时距狄更斯辞世尚不足四十年,但林译狄更斯小说,已经在中国引起极大反响。
1924年11月,林纾逝世的时候,郑振铎对其翻译成就,给了中肯的评价。他在《林琴南先生》中说,“中国数年之前的大部分译者,都不甚信实,尤其是所谓上海的翻译家;他们翻译一部作品,连作者的姓名都不注出,有时且任意改换原书中的人名地名,而变为他们所自著的;有的人虽然知道注明作者,然其删改原文之处,实较林先生大胆万倍。林先生处在这种风味之中,毫不沾染他们的恶习,即译一极无名的作品,也要把作家之名列出,对于书中的人名地名,也绝不改动一音。——这种忠实译者,是当时极不易寻见的。”
其实,不光作为“忠实”的译者,林纾独具风格;他之外的狄更斯译者,那时也几乎凤毛麟角。据国立编译馆《英国小说发展史》记载,截止到1935年12月,总共翻译出版了7部狄更斯小说。除了林译小说,此外就是伍光建译的《劳苦世界》(《艰难时世》)和《二京记》(《双城记》)。它们的译著并不完整,都对原著作了大量删节(张谷若上世纪80年代翻译的《大卫·考坡菲》译文达八十万字,而林纾的《块肉余生述》却只有三十万字)。
尽管“漏译误译触处皆是”,钱锺书还是对林译小说情有独钟。1979年2月,他著文《林纾的翻译》,说“最近,偶尔翻开一本林译小说,出于意外,它居然还有些吸引力。我不但把它看完,并且接二连三,重温了大部分的林译,发现许多都值得重读,……我试找同一作品的后出的——无疑也是比较‘忠实’的——译本来读,譬如孟德斯鸠和迭更司的小说,就觉得宁可读原文”。
第一次以“选集”方式出版狄更斯,或者说完整翻译狄更斯,直到四十年代中期,在左翼进步文学家和出版家的推动下,才得以相继实现。1945年,吴朗西和巴金共同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迭更司选集》,收录了许天虹翻译的《双城记》、《大卫·高柏菲尔自述》(他译的《匹克维克遗稿》,同年由上饶战地图书出版社印行),以及他翻译的莫洛亚《迭更司评传》。1947年,韬奋主办的生活书店外围出版机构骆驼书店,也出了一套《迭更司选集》,其中有蒋天佐翻译的《匹克威克外传》《奥列佛尔》、罗稷南翻译的《双城记》和董秋斯翻译的《大卫·科波菲尔》。此外,狄更斯的中短篇小说也得到进一步介绍,也出现了邹绿芷翻译的《黄昏的故事》(自强出版社,1944)和《炉边蟋蟀》(通惠印书馆,1947)、方敬翻译的《圣诞欢歌》(文化生活出版社,1945)和陈原翻译的《人生的战斗》(国际文化服务社,1945)。这个时期的译者不仅是严谨的外国文学翻译家,而且同时从事进步的文化事业。他们翻译狄更斯的时候,受到了苏联学界的极大影响,比较认同批评家A.亚尼克斯德对狄更斯的评价:“在这社会主义社会中,正在建设一种迭更司只能加以想象的生活。许多他反对的罪恶已在这儿消灭了,其余的也在迅速地逐渐消减灭。这位伟大的写实主义者的作品,使我们的读者回想到了过去的情形,——记忆着这些情形,才能更坚定地建设现在和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