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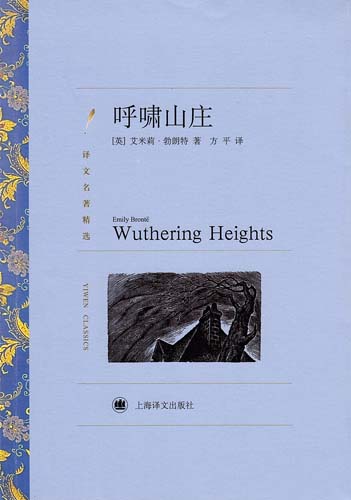 我第一次读《呼啸山庄》应该是在1968年前后。那时候,外面到处都在闹革命,父母担心我出去闯祸,就把我整天关在家里,只要在家,哪怕是把房子拆了也没事。我就稀里糊涂地注意到这么一本书。 我第一次读《呼啸山庄》应该是在1968年前后。那时候,外面到处都在闹革命,父母担心我出去闯祸,就把我整天关在家里,只要在家,哪怕是把房子拆了也没事。我就稀里糊涂地注意到这么一本书。
这个写于十九世纪初叶的为了爱去复仇、爱恨交加的故事对我那个年纪的小孩子来说,简直太有吸引力了。
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无法从小说中摆脱出来,脑海里总是会出现美丽但命运多舛的女主人公凯瑟琳的形象,而更加让我难以摆脱的则是那个叫希斯克利夫的家伙。
再次读《呼啸山庄》的时候,我已经到出版社做了小说编辑。与我第一次读这部小说不同的是,我这时已经具备了一些可以解读这部作品的知识。关于大英帝国、关于资本主义上升期、关于曲折的爱情、关于人性等等。在读这个小说的同时或者前后,我还在读着《红与黑》、《红字》、《傲慢与偏见》、《艰难时世》、《基督山伯爵》、《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等。
英国的文学非常特殊。这是一个尊重传统,视传统为尊贵的特殊民族,不要说写《呼啸山庄》的艾米丽·勃朗特,就连比她名气更大的作家狄更斯一开始都得不到认可。勃朗特三姐妹的出世可以说完全是出于对世事的无知,她们勇敢地写作,像《呼啸山庄》那样的作品刚刚问世的时候曾经在英国引起过巨大的风波和争议,这一点与狄更斯的境遇也差不多。
《呼啸山庄》采用的是一种戏剧的手法来写的,这一点在喜欢正襟危坐的英国人那里简直太叛逆了。那种写法后来便很普及了,曹禺先生写《雷雨》时采用的就是这样的手法,即戏剧大幕一拉开,故事已经展开,甚至都接近高潮了,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都是通过剧中人物的交待逐步为读者所掌握。
艾米丽当初采用这样的手法来写小说,在很多传统作家看来,简直是开玩笑。与狄更斯经常在小说中使用那些下里巴人肮脏粗俗的语言一样,艾米丽的这种做法也引来英国传统派守旧派的谩骂。
英国大作家当中像伍尔芙、毛姆等都给艾米丽以极高的评价。伍尔芙说,小说中被描写的“我爱我恨,是全人类的”。毛姆则说,“我不知道还有哪部小说中爱情的痛苦、迷恋、残酷、执着,曾经如此令人吃惊地被描写出来”。艾米丽的创作终于被世人所认可,英国文学也像改正了对狄更斯的认识一样,纠正了对艾米丽“非主流”的看法。
《呼啸山庄》曾十几次被英国和美国拍成电影,其影响力可以说是长盛不衰。上海翻译家方平先生将这部经典作品翻译成中文时,我曾就翻译当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向他讨教过。方平先生对英国文学有着深入的研究,他说英国这个国家在文化上有特点,那就是要他承认新的东西很难,但是,一旦承认了,就立即要全世界都跟着喜欢。当年狄更斯出世,很多英国文学家都认为大逆不道,可是最后在英国作家中肯赏以文豪桂冠的也只有狄更斯一人。
多少年过去了,《呼啸山庄》依然是我喜爱的英国小说,我还在一个劲地收集这部小说的各种中文版本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