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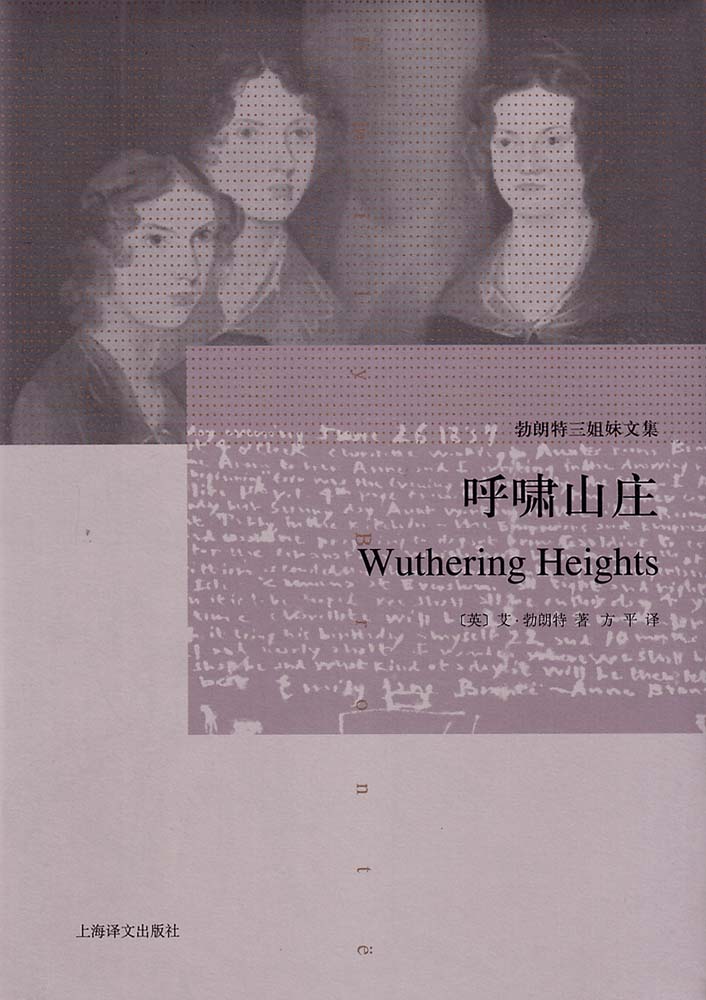 隔了将近四十年流逝的时光,我还能记得当初阅读《呼啸山庄》时年轻的心灵所感受到的那一股直扑而来的冲击力量:放不下手中的书,却又不得不时时停顿下来,透一口气,好舒缓一下过于激动的心情。有一些文学名著,我特别喜爱,读过三遍四遍;但是这一部我最喜爱的杰作,却从没有读过第二遍——不敢去惊动保存在心坎里的最初的印象。当然,后来我咀嚼它、研究它,又翻译它,但那是伏在案头的工作,不是在享受读书的乐趣了。 隔了将近四十年流逝的时光,我还能记得当初阅读《呼啸山庄》时年轻的心灵所感受到的那一股直扑而来的冲击力量:放不下手中的书,却又不得不时时停顿下来,透一口气,好舒缓一下过于激动的心情。有一些文学名著,我特别喜爱,读过三遍四遍;但是这一部我最喜爱的杰作,却从没有读过第二遍——不敢去惊动保存在心坎里的最初的印象。当然,后来我咀嚼它、研究它,又翻译它,但那是伏在案头的工作,不是在享受读书的乐趣了。
介绍这部杰作一直是我的心愿。为了做好准备,我收集了包括“牛津版”,“现代丛书”插图本在内的四五种本子,前后试译过几次。在十年动乱中,书籍最容易和人一起遭到劫难,我收藏的这些原著只幸存一种:苏联版的英文本。这自然不是个理想的版本,但我依靠它开始认真翻译起来:修改旧译,续译了近二十章。在当时恶劣的环境中不敢奢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译文公开发表的一天,我最大的梦想也只是让自己的心血有一个小小的成果:装订成一册整整齐齐的手抄本。为了便于保藏,便于在爱好文艺的朋友们中间私下流传,双面誊写的手抄本字迹十分紧密。
当初勃朗特三姐妹在她们寂寞的童年时代,为了满足精神生活的需要,不让人知道,办起“地下刊物”来,在两英寸的小本子上拥挤着密密麻麻的小字。我看着自己的难见天日的手抄本,很惭愧,很感慨,哪儿想到,在将近一个半世纪以后,我,一个五十岁边缘的中年人了,没有一点孩子气了,却为了寻求精神上的寄托,做的事竟跟那三位早熟的英国女孩子差不多。
人在他的青少年时期总是对未来抱着形形色色的幻想,但不一定都能一一实现。现实往往是无情的。现在,经历了几番大起大落的人事沧桑,当初四十年前萌发的一个卑微的心愿,竟然有幸得到实现了,我感谢命运,给苦涩的回忆添上了几丝自我安慰的甜味儿。
需要交代一下原书的版本问题。
《呼啸山庄》的初版本(1847)是一个排印得很糟糕的本子,1850年再版,艾米莉·勃朗特已故世,姐姐夏洛蒂花了不少心血,为之写序,写作者简介,并作了仔细的校订,在标点、段落上也有很大更动。长期以来,这个校订本被看作定本,《呼啸山庄》的各种版本(包括我过去收集的几种本子)都以它为底本。
但是从本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当初根据艾米莉手稿排印的初版本得到重视,编家开始改用初版本作为底本(当然参照再版本改正误植),现在我手头所有的三种现代版本:“矮脚鸡版”(Bantam,1981),“企鹅版”(1984),“牛津版”(1985),全都以初版本作为底本了。“企鹅版”的编者这样说:“我们要的是艾米莉的标点和段落,不是夏洛蒂的标点和段落——当然,我们并不要排印得十分马虎的初版本上的那许多误植。”这几句话也许相当普遍地表达了当代编家们的意见。
为什么“要的是艾米莉的标点和段落”呢?可以从第一章中举个例子:洛克乌到呼啸山庄做客,受到冷遇,只有几条恶狗跟他做伴——恶狗开始向他进攻,先是一条,接着是一群向他扑去——被围攻的洛克乌大声告急——主人和仆人却若无其事,依然不慌不忙,在爬地下室的梯子——幸亏这时候冲来了一个健壮的厨娘把恶狗打退了。(见第8页)
如果把这充满了动作的小插曲,改编成电影剧本,可以分切成好几个不同角度的镜头;艾米莉也的确把叙述分为四段(等于电影中运用四个分镜头来表述),但是夏洛蒂在校订过程中却把它们合并成两大段,她没有意识到这样一改动,紧张的节奏感就松弛下来了。
又如第九章结尾,说到林敦在父亲去世三年之后,领着新娘到教堂结婚;而上文说的是卡瑟琳的兄长一心巴望妹子嫁到林敦家去,好替娘家增添光彩。上下两段之间有一个很大的时间上的跳跃,交代的又是两户人家的事;可是再版本中却把这两段文字合并在一起了,这不是胡子眉毛一把抓吗?
这类例子是大量的。我们长期受到电影艺术熏陶的现代读者可以肯定地这样说:在情节向前推进的过程中,原作者表现的节奏意识比修订者强多了。现代版本恢复初版本的面貌是有充分理由的。
在我国半个世纪以来的几种中译本中,拙译由于晚出,有机会利用当代英国学者们版本研究的新成果,可说第一次在艺术形式上反映了原作的明快的面貌。
在英国古典文学中,《呼啸山庄》一向被认为是最难理解的作品之一,有人把艾米莉·勃朗特称作“我们现代文学中的斯芬克斯”,这是说,她是个猜不透的谜。英国评论家塞西尔在论述本书时提出了很精辟的见解,但他向我们描绘的女作家是个离得我们很远、不食人间烟火食的“神秘主义者”。
严肃的学者像凯特尔以他所信奉的阶级斗争的学说去阐述作品的主题思想。他的论点在我国有较大的影响。女作家的创作意图是什么?凯特尔并没给予很多考虑;我觉得他不是帮助读者去理解、接近作者,而似乎是帮助作者披上现代化的服装来取悦读者。
在西方很时髦的性心理学也应用到研究《呼啸山庄》上来了。英国小说家毛姆介绍给我们的艾米莉竟是一个由于遭到拒绝而有着精神创伤的同性恋者!真是众说纷纭,五花八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