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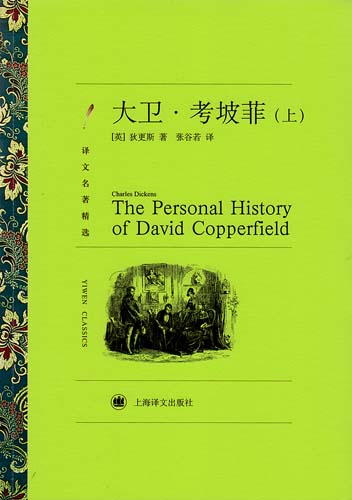 狄更斯,一位令后世史学家常常要以他的名字来为其生活的时代命名的小说家,是否担当得起“伟大”二字?一个多世纪以来,有如此之多的读者追读狄更斯的文字,原因何在? 狄更斯,一位令后世史学家常常要以他的名字来为其生活的时代命名的小说家,是否担当得起“伟大”二字?一个多世纪以来,有如此之多的读者追读狄更斯的文字,原因何在?
曾经身为童工、律师行杂役的狄更斯,下笔便写出了那个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中小人物的悲欢;记者经历使他练就了一副描绘市井社会众生百态的绝妙笔墨;他对法律的了解也令读者惊讶不已……也许狄更斯算不上天才式的作家,他生来就是为芸芸众生写作的,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正如同其它许多时代一样——它们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
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
倘若今天沿街做一次随访,请路人为查尔斯·狄更斯这位二百年前出生的作家贴个标签,多数中国读者的第一反应,恐怕仍是那个多年来印在教科书上的“经典”定义——“伟大的英国小说家、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不过肯定也有人会对此不以为然:狄更斯是一位伟大的小说家吗?
在众多“现代派”的眼里,他不过是一名至多二流且早已过气的畅销书写作者,难以跻身“伟大作家”的行列。事实上,早在利维斯写作他那本著名的《英国小说的伟大传统》时,就已经将狄更斯的名字剔除在外。这一意味深长的选择引发了后世的长久议论,有论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狄更斯作品中突出的伤感情调使他显得很不“英国”。的确,狄更斯尽管继承了英国文学中“夸张”的传统,但其作品的浪漫主义基调,却实在是绝大多数的英国小说所不具备的。
可是为什么那么多年来,就是会有那么多读者,包括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读者迷恋狄更斯?这真是一个谜。而世上又有哪一种迷恋,不是一个难以捉摸的谜呢?
一个世代的创伤
想要破解这个谜,跟随着狄更斯的文字回到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应该是一条可能的路。
“成为一位成功作家的必要条件是,有一个不幸的童年。”这句话用在狄更斯身上真是对极了。狄更斯1812年出生于英国朴次茅斯,十岁那年全家迁居伦敦,自此他就与这座工业革命时代的典型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狄家早年生活尚属小康,后来因为双亲用度无节制,欠下高额债务,导致父亲入狱(在狄更斯生活的时代,因金钱债务被判入狱者数不胜数,简直成了一大社会问题),一家人随即迁至牢房居住,少年狄更斯则被送到伦敦一家鞋油场去当学徒工,每天工作时间长达十小时以上,还要饱受凌辱。日后,从《大卫·考坡菲》到《艰难时世》再到《远大前程》、《小杜丽》,在狄翁众多作品中,都能见到当年这段痛苦经历的影子。正如在《艰难时世》中,斯蒂芬·布克莱普尔向富商庞德贝抱怨的:“工厂主们威胁和压制工人,仿佛他们是机器,没有爱好,没有记忆,也没有灵魂。”而《大卫·考坡菲》里男主人公的遭遇,则压根就是作者本人当年生活的真实再现。
幸好,如此恐怖的生活状态并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父亲继承的一笔遗产终于令狄更斯一家的经济状况有所好转,狄更斯于是有机会重返学校。不过好景不长,随着他15岁时从威灵顿学院毕业,狄更斯再次面临需要在底层摸爬滚打的现实。他先后担任过实为杂役的所谓“律师助理”和法院的庭审速记员。在这里,狄更斯有机会从另一个角度接触社会,他几乎是即刻体验到了当时社会的光怪陆离,尤其洞察了所有那些光鲜外表下的破败景象:他笔下的律师会馆“被伦敦所有贫穷却死要面子的破落户们不约而同地视为胜地和日常避难所”,“它总是挤满了人,啤酒和烈酒的蒸汽不断升上天花板,经过热力的浓缩后,像下雨似的从墙壁上流下来;每次开庭时那里汇集的旧套装,比十二个月送去杭兹迪奇旧货店卖的还要多……”他也曾在《老古玩店》里,以略显刻薄的笔触,描写女法律人萨丽·布拉斯的童年游戏:“当她还在牙牙学语时期,就已经表现出一种非凡的才能,能够模仿一个执达吏的走路和神气——当她装作这个人物时,她学会了敲打她那些小同伴的肩膀,并且把他们送到假想的监狱,样子足够逼真,看到她表演的人都感到又惊愕又好玩;更妙的是,她能把这一切惟妙惟肖地在她的木偶中执行,将一堆小桌椅逐一清点登记。”寥寥数语,就使一个在不知不觉中深受法律“熏陶”的稚童形象跃然纸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