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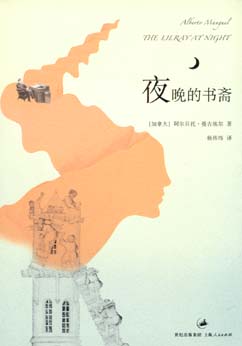 阿尔贝托·曼古埃尔为读书人熟悉是因为他的《阅读史》,而去年出版的《恋爱中的博尔赫斯》让更多的读者知道他和博尔赫斯的交情。近日,曼古埃尔的新书《夜晚的书斋》引进出版,承接他写作一贯的关注点,仍是讲述关于书的故事。本期《晶报图书评论》将从曼古埃尔的关键词开始,打开他与他的阅读世界。 阿尔贝托·曼古埃尔为读书人熟悉是因为他的《阅读史》,而去年出版的《恋爱中的博尔赫斯》让更多的读者知道他和博尔赫斯的交情。近日,曼古埃尔的新书《夜晚的书斋》引进出版,承接他写作一贯的关注点,仍是讲述关于书的故事。本期《晶报图书评论》将从曼古埃尔的关键词开始,打开他与他的阅读世界。
关键词 不安全感
“我们的历史是一段漫长、黑暗、不公正的故事,”出生于阿根廷的作家阿尔贝托·曼古埃尔说,这种不安全感在早年一直萦绕在曼古埃尔的周围。
出生于1948年的他不断地陷入这种政治漩涡,那是阿根廷历史上的黑暗时代,也是他无趣的童年。1955年他的父亲被推翻庇隆的军政府逮捕了,对了,就是那个把博尔赫斯降级为市场禽兔稽查员的庇隆将军的政府。随后一个政变接着一个政变,总统来一个走一个,政治一度成为了生活的常态和学校的常规教育模式。对于青春期的曼古埃尔来说最大的乐趣就是在去学校的路上看一辆辆的坦克轧过马路。很奇怪的是,在1968年离开阿根廷之后,曼古埃尔似乎很少提及他早年的这些历史。现在已经是功成名就的作家、翻译家和藏书家的曼古埃尔生活中大部分的乐趣是沉迷于梳理和阅读他的藏书。他的作品从《阅读史》到最近的《夜晚的书斋》,基本都关涉于体验式的阅读与收藏,是一种纯文学性质的作品,与政治基本无关。他似乎有意逃避早年的生活经验,或者说下意识地选择性地遮掩住了那段无趣的童年。
但在那段黑暗的时代中总有一些值得涂抹的亮色指引着向往希望的方向。曼古埃尔早年生命中值得记忆的两个时刻:一个是1960年,高二开学的第一天下午,他遇到了一位老师:“他走进教室,仅仅说了下午好,没有告诉我们课程是什么或者他的期望是什么,就打开了书,开始阅读一段话。”那是卡夫卡的《城堡》中的一段,之前他从没听说过卡夫卡,但那个下午,文学的大门訇然中开,“这和我们必须学习的五六年级课本里干巴巴的经典片段不同:它神秘又丰富,还打动了我们从不知晓的灵魂深处”。这一时刻在一个少年本已经枯荒的心里种下了文学的种子。而在曼古埃尔生命中另一个重大事件就是与博尔赫斯的相遇。
关键词 博尔赫斯
那是1965年,曼古埃尔在一家书店放学后做临时工。已经失明的博尔赫斯在他母亲的陪伴下走进了书店,“他把书拿起来碰着自己的脸仿佛鼻子能吸入再也看不见的文字”,曼古埃尔对这位有些奇怪的顾客印象深刻。而后的一天,博尔赫斯询问他是否愿意傍晚的时候去为他读书,因为他的母亲年纪逐渐大了,容易疲劳。年轻的曼古埃尔接受了这一请求,于是在随后的许多个夜晚他为博尔赫斯读了斯蒂文森、吉卜林、但丁的各种注释版本等等。博尔赫斯的习惯,在阅读中会打断并加入自己的评论。曼古埃尔还没有意识到这个过程对他是一种奢侈的荣耀:能够亲自聆听一位大师对各种经典的解释和评价。他们在一起除了读书还会去散步,闲聊居住的城市,去看电影——曼古埃尔会把看到的画面描述给博尔赫斯,然后博尔赫斯会发表他的评价——于是在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出来的电影院中,你总会发现很多观众会对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和一个失明的老人之间的窃窃私语怒目而视。
遭遇博尔赫斯是曼古埃尔生命中最值得回味的大事。事实上,如果你阅读过曼古埃尔的《阅读史》、《阅读日记》、《恋爱中的博尔赫斯》以及新近的《夜晚的书斋》等作品,你总会从字里行间发现博尔赫斯的影子。博尔赫斯对书籍的痴迷是众所周知的,他失明之后还源源不断地购买图书,摆满自己的书房。曼古埃尔在这方面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这样并不是说曼古埃尔仅仅继承了博尔赫斯表面的形式,在浩如烟海的阅读方面,在博闻强识的写作方面,在翻译和虚构小说方面,曼古埃尔把博尔赫斯的品质发挥得淋漓尽致。也许很多人会对这种模仿不以为然,以为最终他无法走出博尔赫斯的影子。但博尔赫斯会这样认为么?博尔赫斯认为,有人之所以小心翼翼地模仿一个作家,是因为他不由自主地把这个作家当成了文学,是因为他认为脱离他一分一毫便是脱离理性、脱离正统,是因为几乎无限的文学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当然,无论在曼古埃尔还是在我看来,博尔赫斯就是这个人,这个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