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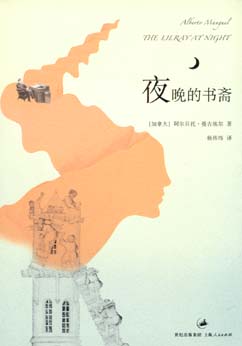 我既惊诧女图书管理员的敬业,更惊诧德军飞行员的冷静,是战争使得“有借有还”这么寻常的小事,变得不寻常起来——书的价值在此刻超越了人的生命价值。 我既惊诧女图书管理员的敬业,更惊诧德军飞行员的冷静,是战争使得“有借有还”这么寻常的小事,变得不寻常起来——书的价值在此刻超越了人的生命价值。
15年前,我们的阅读指数远没有今天幸福,15年后,我们的阅读指数很幸福,我们已不满足于我们自己人写的藏书文章了,不断地有国外的藏书家的专著被翻译进来,一本接一本,我自己已攒了30多种,宛如一个集书的专题了。最新的一本是《夜晚的书斋》,作者阿尔贝托·曼古埃尔,我多年前买过他的另一本书《阅读史》,封面很抓眼,还记得是大热天在琉璃厂商务印书馆门市部买的,而且只剩一本,不能挑品相了,当年我们的购书指数也不如今天幸福。
夜晚的书斋总是被赋予神幻莫测的色调,余秋雨称夜幕低垂中的书房是他“精神的道场”,杜渐说他20年来每天夜里都坚持二小时“一字不拉”的看书,而蒙田却说“我在那里度过了生命中的大多数日子,一天中的大多数时间,但是夜里我从来不到那里去”。夜晚是分两部分的,晚在夜之前,夜于晚之后,通常天黑了就算是晚上了,而夜的开始应是23点以后,对于某些善于熬夜的人来说,夜的概念还要晚一些,1点钟我觉得才进入状态。我说过一句话:“为什么我迟迟不睡,因为此一睡去,生命又少了一天。”周作人是不熬夜的,他说:“从前无论舌耕或是笔耕的时代,什么事只在白天扰攘中搞了,到了晚饭之后就只打算睡觉。”还说“不喜‘落夜’或云熬夜。我不知道是白天好还是黑夜好,据有些诗人说是夜里交关有趣,夜深人静,灯明茶熟,读书作文,进步迅速,我想那一定是真的”。(《夜读的境界》)周作人说的“交关”是上海话,是“很”和“非常”的意思,周作人这篇短文刊在《亦报》——《亦报》在上海出版。夜晚书斋的功能和白天的书斋没什么两样,都是用于读书和写作的,因为夜深所以人静,而安静在白天无处藏身。
我原以为《夜晚的书斋》是像书名所说的那样的一本书——是属于夜晚的,是属于书斋的。我错了,错了多一半,这本书几乎省略了夜晚与白昼的差别(夜晚只是一个由头),这本书也没有自闭于一己一屋的书斋(更多的是说公立图书馆)。这本书太丰富了——甚至有点儿过于丰富了,有关图书的一切它似乎都讲到了,理念满天飞,接受起来很有点儿难度,我算是很喜欢西方作家的句式了,他们很少有多余的话,他们的话很具哲理性。
通常的读书心态是求同的——一看到作者的观点与自己一致,便欣欣然称好,尤其当这是一本谈书及书房的书,对我而言一致的地方远多过不一致的地方(当然,很多的观点我是第一次听说,还来不及想一致还是不一致)。存书比较多的人都遇到过找书难的问题,甚至有这样极端的例子,费了半天劲找不到的书干脆再去买一本新的(滑稽的是,刚买回新的旧的那本又钻出来了)。本书作者说:“我想像中的书架,矮的一格从我腰部开始,逐渐升高到我伸出手臂用手指够得上为止。根据我的经验,书籍如果高到需要用梯子的程度,或者低到强迫读者趴在地板上才看得清楚,那就无法取得人们的注意了,不管它们的主题和优点是什么都没有用。”止庵先生称书架第二排的书为“死书”,有形同无,某些书终其一生都没被主人阅读过,某些书命中注定要在架子上站一辈子的岗。
书房的面积与图书的增速,永远是一对矛盾,在这一点,私家书斋和公立图书馆均不能幸免。私家处理矛盾的方式无碍他人,把多余的书卖掉或卖给谁别人都管不着,贵卖还是贱卖自己说了算。公家图书馆就不该那么随意了,我原来以为他们是慎重从事的,事实却令我吃惊。书放不下,办法之一是盖房子,之二是淘汰书。图书馆常年都在“剔除”书(多为复本),我手里就有盖着“剔除”章的图书馆藏书。前几年炒得沸沸扬扬的“巴金捐书沦落地摊”事件,受捐者是全国有影响的大图书馆,其实是正常的“剔除”复本,只是因为书是巴金的书,事情就演变为事件了。这次事件使得这家大图书馆变得异常过敏,有一次我送某书给拍卖行,某书盖有这家图书馆前身(馆)的藏书章(解放前),他们居然质问我某书的来源。现在图书馆用显微胶片来拍摄珍贵的不易保存的古书及古旧书报杂志已很普遍,简称“微缩”,阅读微缩之书报还须一种特殊的仪器,很不方便。微缩之后的报刊应该是安全了吧,谁料到,它们的下场竟也是被清理出宫甚至毁掉,理由均是“地方不够”,当我看到《夜晚的书斋》里这样的情节,我在下面写道“啊,我只剩下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