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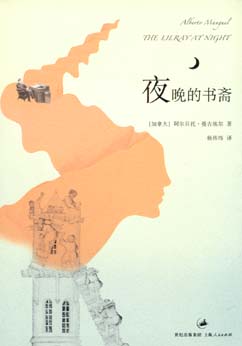 核心提示:曼古埃尔是一位早熟的、不知疲倦的读者。他的写作方法就是自由联想外加现学现卖,他急吼吼抓到手里的是深奥偏僻的零头碎脑儿。 核心提示:曼古埃尔是一位早熟的、不知疲倦的读者。他的写作方法就是自由联想外加现学现卖,他急吼吼抓到手里的是深奥偏僻的零头碎脑儿。
自己写不出书评时,最好读读别人写的书评——这是我一直以来遵循的一个原则。《夜晚的书斋》在案头摆了两个多月,我时常对着它淡青色的封面发呆,书早就读完了,可是似乎没什么可再向别人介绍的。于是,我乞灵于万能的书评家们,他们对任何话题都有得可说。指责我取巧也好,嘲笑我无能也罢,反正我认为把英美方家的书评引介过来,比我自己搜索枯肠没话找话好得多。为节省读者的时间计,我在每则书评片段后都缀上数语,不指望“谈言微中”,只是想把人家的苦心与曲笔勾勒得更清晰一些。
一、如何介绍作者
“作为一个书话家,阿尔贝托·曼古埃尔也许会被人与罗伯特·伯顿或艾萨克·迪士累利(Isaac D'Israeli)相提并论,不过,他行文不似《忧郁的解剖》的作者那般奇僻古奥,也比《文稗类编》(Curiosities of Literature)纂辑者的文字浅易可读。不能不提的是,他的交际面可比前面两位广多了。事实上,想在当代文人里找到一个比曼古埃尔人缘更好、游历更广的,几乎不可能了。1948年,曼古埃尔生于阿根廷,在塔希提度过一段青春岁月,在多伦多的二十年间雄踞加拿大文坛一方,此后转战欧洲。因此,他不仅会用不无抒情格调的英文写作,还可以自如运用西班牙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也许还有乌尔都语、皮克特语和亚拉姆语)。最重要的是,他跟伯顿和迪士累利一样爱读书,读啊读,读了之后就评自己所读之书、引自己所读之书。”——迈克尔·德达(Michael Dirda),载2008年4月6日《华盛顿邮报》
熟悉英美评论界的人肯定知道,迈克尔·德达长年执掌《华盛顿邮报图书世界》编务,是书评圈里有名的一言九鼎的人物。他跟曼古埃尔一样,也是“爱读书,读啊读,读了之后就评自己所读之书、引自己所读之书”。由他来评曼古埃尔的书,虽曰得宜,但毕竟干的是同一行当,言语间流露一丝半点同行相轻的味道,恐怕也是难免的。“交际面广”(sociable)拿来形容读书家,自是罕见的用法。“雄踞加拿大文坛一方”也极惹人遐思。至于藏在括号里的“乌尔都语、皮克特语和亚拉姆语”云云,则是露骨的揶揄了罢?
二、如何展开评论
“斯威夫特设想过书籍之间的大战。在他的一首讽刺诗中,书斋里的卷册不是安躺在书架上,而是满屋子地追打叫骂,相互撕扯书页以泄愤。然而,当灯光熄灭,情形又如何?没准儿这些好斗的书籍会偃旗息鼓,上床造爱,孕育下一代的书。作家写书,因为他们是阅读强迫症患者;作家写书,在环壁皆书的房间里完成。别再相信什么‘艺术模仿人生’了:文学不过是一种自我繁殖、自我指涉的活动而已。阿根廷的读书家阿尔贝托·曼古埃尔(著有《阅读史》等),在这个惬意的封闭小圈子里算是个专家,富有象征意味的是,他将自己的书斋建在卢瓦尔河地区一座15世纪建成的谷仓里。他就坐在那儿,最好是夜里,此时黑暗已将外间‘浩瀚无形的宇宙’隐去。在灯盏洒下的柔光的照耀下,他甚至不必去读书,仅仅是书架的木头味和‘包书皮革的麝香味’就足以让他感到安恬、令他产生睡意。尽管从起皱的书页和他干燥的皮肤上有‘浮尘’细细飘落,预示着这一觉睡去不会太短,可是他不介意。书斋就像分了若干层的坟墓,曼古埃尔乐得在坟堆里筑屋。”——彼得·康拉德(Peter Conrad),载2008年4月27日《观察家》
这鬼气森森的开头,亏得书评家想得出来。彼得·康拉德今年六十岁,在牛津教英国文学已教了三十多年,他的书评散见英国各大媒体。别只顾着欣赏人家细腻的文笔,所谓“听话听音儿”,得留心其引入正题前的语气铺垫。表面上,书评家一上来谈的是斯威夫特,其实“作家写书,因为他们是阅读强迫症患者”、“文学不过是一种自我繁殖、自我指涉的活动而已”这类判断都是针对着曼古埃尔来的。尽管不明讲,可是若换了另一个评论对象,彼得·康拉德兴许不会对写作、对文学做如是总结。实心眼儿的读者若是断章取义,将上面这类判断认作书评家文艺观点的剖白,那可就大错特错了。最绝的还是那句“他甚至不必去读书”。确实,“夜晚的书斋”又何必非与“读”扯上关系不可?轻抚书脊,细嗅书页,静待睡神降临,对某些人来说,就可以是完美的书斋夜晚。
|